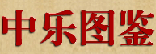编者的话:
2017年10月29日“上海书评”发布了一篇对上海音乐出版社资深编辑樊愉的图文采访。作为樊紫云、樊少云、樊伯炎三代琵琶世家的后人,樊愉是琵琶艺术流派“瀛洲古调”(崇明派)的第四代传人,他也是古琴界名家。这篇采访中樊愉在娓娓道来中呈现了近现代国乐人的一幅生态画卷,许多细节鲜为人知而朴实生动,折射出了国乐前辈们的真性情以及情感、情操和情怀,蕴含着20世纪中叶前后浓郁的社会文化风情,在此转发以飨同道。
(以下原文)
樊愉谈樊家艺术往事:父亲的笑笑楼曾是老先生们的据点


樊愉(蒋立冬 绘)
用樊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大概要算是最熟悉上海古琴界的人之一了。还在孩提时,他就随着父母一同参加老先生们的聚会,等到成年之后,自然而然地便从事音乐相关工作。事实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樊家形同文艺沙龙,曲界、画界的老辈名流,都到此地聚会。樊先生的父亲樊伯炎、祖父樊少云都是身兼数艺之长,如书画、昆曲、琵琶、古琴等;母亲庞左玉出身名门,是近代中国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女画家。从樊先生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可以看到那个逝去的时代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迷人细节。
采访︱郑诗亮 何宇婷(实习)
此前读过您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您的祖父,他既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曲家。正好顺着这个话题,能请您谈谈您家庭的情况吗?
樊愉:我祖父樊少云是吴门画派的画家。他的爱好有很多,又很喜欢拍曲,所以我的父辈们都擅唱昆曲。他还喜欢古琴,1936年同在苏州的琴人们创立了今虞琴社,后来因为上海古琴爱好者来往不方便,同年12月成立了今虞琴社上海分社。


樊少云


《樊少云昆曲画册》画《艳云亭·点香》,张允和书曲。
我们祖籍在崇明,曾祖父当年是画喜神的,也就是给去世的人画像,于是我祖父就跟着我曾祖父学画,他后来又拜陆恢为师。我祖父不仅画画,还传承了崇明的瀛洲古调派琵琶。我祖父全家在1910年代搬到了苏州,当时的吴中一带是文化中心,我祖父那时在吴中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不过,苏州从抗战之后就慢慢衰退了,许多文化人都迁居到了上海,于是我祖父一家人也来到了上海,当然,包括我父亲。
您父亲大约是什么年纪随您祖父来的上海?
樊愉:他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大概二十几岁,在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跟着平湖派琵琶家朱英专修琵琶。在此期间,庞虚斋又邀我父亲去他府上临画。现在很多人一直以为庞虚斋身边的张大壮、吴琴木等人在帮庞虚斋理画,其实除了陆恢这样的人还有点资格帮他理画,其他人还没有这样的资历,包括我父亲。


樊伯炎
庞虚斋在苏州的典当行和我祖父家是门对门,他也知道我祖父是陆恢的学生,就把我父亲请到他那里,每逢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给一些报酬。庞虚斋其实也是为了培养年轻人,经常拿出自己收藏的古画给一些年轻人临,比如张大壮等人,当然还有我母亲庞左玉。


樊伯炎、庞左玉合作《萍柳图》
您父亲当时在庞虚斋那里主要做哪些事情,他和您谈起过吗?
樊愉:据我父亲回忆,庞虚斋除了在绘画上培养我父亲,学习书画鉴别和临摹他的藏画,另外,就是帮他代笔应酬。
那您母亲的情况呢,能请您谈谈吗?
樊愉: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我父亲和母亲成婚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都是画界的同行。自从1934年中国女子书画会成立起,我母亲一直是积极参与的成员,当时的发起人有冯文凤、顾飞和陈小翠一群所谓的“闺秀画家”。女子书画会自打成立起,直到1949年,大概一共开过十三次画展,只在抗战上海沦陷时有停顿。我母亲除了参加女子书画会的画展,还多次开个人画展。那些女画家通过画展来“推销”她们的作品,可以让自己在经济上独立。


庞左玉像
我母亲和陆小曼、陈小翠关系很密切,“文革”期间还和陈小翠对换了房子,陈小翠在1968年用煤气自杀,大概是对我母亲有点心理暗示,第二年她也走了这条路。那一两年里,文艺界的自杀风气很盛,实际上是江青对上海文艺圈的迫害,因为知道她当年在旧上海的事情的人不少,当时的《申报》上有关演员蓝萍的事多着呢。


庞左玉画《翠荷图》
我母亲有一件事是上海画家当中没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各领事馆的外交官太太们学画中国画,都是由我母亲上门教授的。因为解放之前她就有过教外籍人士学画的经历。我还记得当时我母亲教过一位朝鲜领事的太太,她画得真好。其实这项工作是国家安排的任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个女的来家里找我母亲谈话,她们究竟是哪个部门的不清楚,而且谈话的内容连我父亲都不能询问。我想,无非是要我母亲向她们汇报领馆教画的情况,从中打探点消息。“文革”一开始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因此这件事也成了我母亲“文革”中的“罪状”之一。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活动频繁,而您家人从事的都是传统艺术,这对他们的影响大吗?
樊愉:我一直觉得,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国民间艺人来说,确实是件好事。不管是演员还是画家,特别是北方的相声演员,工作有了着落,生活也有了保障——可能南方评弹演员是个例外,因为他们之前的收入比较高。不过现在想来,这种被国家养着、缺少市场竞争的环境,可能对艺术创造力会有损伤。六十年代,我母亲还去搪瓷工厂画脸盆、暖水瓶,在布厂给印花布点花心,因为当时的印花布上的花心不能拿工业用黄色涂料去点,容易腐烂,所以就让画家用赭石去点花心。这个工作看起来辛苦,我母亲反倒觉得很轻松,因为不用动脑子,就是手上的动作,又能和工人聊天,挺开心的。我母亲画的几个脸盆,我现在都还保存着。其实,对他们来说,自己的画作能在工业品上出现还是蛮新鲜的,以前几十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还是挺乐意的。


庞左玉画的脸盆
现在硬要说当时艺术家有多么痛苦,这也不完全准确。那个年代,我父母这一辈人中确实有些艺术家认为,自己以前弄的都是些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东西,不合时宜了。不过,老一辈昆曲演员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那些传统老戏不能再演,他们从小学的一身本领无处可用,那真是很痛苦的。我父亲曾开玩笑说:“那些传字辈的老先生唱《东方红》《国际歌》都带着昆腔。”
那么,当时您家里人的去向是怎样的?
樊愉:有朋友曾经对我说过,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首批聘任的画师一共六十多人,你们家就占了两人。的确是这样,我祖父和我母亲是第一批进画院的。我祖父因为年纪大了,算是不负实职的老年画师。我父亲1956年也进了上海戏曲学校任教,教出了不少音乐的学生。总之,生活都稳定了。“文革”之前的几次运动,像“三反五反”、“四清”运动,老实说对文化人的冲击并不大。
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您家里人是怎么一种状态呢?
樊愉:那个时候什么活动都停止了,大家也都不来往了。我看过一些描述当时情况的文学作品,说“文革”时期有人在家里偷偷地弹琴唱歌——当然是指从事专业的人。我觉得这带着浪漫色彩,其实是一种美化。当时的情况基本不太可能这样,因为玩琴棋书画这些东西是需要心情的,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况且以当时的住房条件,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你,你生活有点变化,别人就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或一般职员倒是有可能。但是一到了1976年以后,所有东西一下子都回来了,一切都在慢慢恢复。


樊少云晚年在画室
前面聊了很多您祖父、父母亲的事情,之前读您的文章,看到您姑母也都画画,她们的情况您可以谈谈吗?
樊愉:我有两位姑母。她们从小就随我祖父学画,唱昆曲,都画得很好,唱得也很好,又是尽心尽责的家庭主妇。我二姑母樊诵芬也是当年女子书画会的成员,她留下来的画还挺多的,又随大曲家殷震贤拍昆曲。《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的作者还来采访过她,那时她八十六岁,九十岁时去世了。还有我一位叔叔,樊书培,他是北京建工学院的建筑教授,他的昆曲功力可不得了,能唱能演,少年时随名家俞振飞、沈传芷、李荣圻拍曲,晚年成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重要人物。他们现在都不在世了。
这样说来,您的祖父、父亲和母亲,现在还没有专书来记载他们,有点可惜,您有写作打算吗?
樊愉:如果单篇写我祖父,或者我母亲、父亲和其他长辈,不太好写。当然最好写成一本书,把他们都写进去,因为有些人物和事件之间都是有交叉、有关联的。他们涉及的艺术门类又多,有书画、昆曲、琵琶、古琴等等,交往的人也极多。要是由外人来写,很难对事实有全面了解,我也不一定满意。我倒不怕人家说坏话,主要是希望写出来的内容能够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这一辈人的缺点,我还是清楚的,不会一写到他们好像就是完美无缺。我试着做吧。
这些缺点,具体指的是什么?
樊愉:他们的缺点来自他们那个时代,这是逃不脱的。特别是我父亲,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艺术做到极致,只是当作一种修养、一项爱好。可有些老先生却做到了。比如东南大学的王守泰老教授,他是汽轮机的专家,他继承了家学的昆曲,对昆曲的研究非常精深,写过一本《昆曲格律》,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他发起、组织各地的曲学家,编著了一部《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我父亲也参与其中。我们家里可能是上一代人的成绩比较突出,到了下一代反而有点受压制,出不来了,因为知道自己追不上前一辈——我指的主要是著述方面,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您父母横跨几个不同的文化圈子,交游广阔。经常与您父母来往的朋友有哪些,您还有印象吗?
樊愉:因为我后来学了音乐,对音乐这个圈子比较熟悉,特别是今虞琴社。因为我五六岁起就跟着父母同张子谦先生与今虞琴社一起玩了,后来我又学了琴。现在要说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海古琴界的人,大概我要算一个了。我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的。


樊愉童年与母亲庞左玉
比如,古琴家黄渔仙是我父亲的义母,我从小是她带大的,相当于我的干祖母。她的嗣子就是当年《申报》“自由谈”的名编辑黎烈文,与鲁迅有交往。她讲到鲁迅时会说:“很讨厌,他总是带一个女人过来。”这指的是许广平,按照她那一辈人的看法,鲁迅的正妻就是朱安,老太太很难理解后来人的自由恋爱。再比如,邓怀农大家都知道他是画家,其实他也会弹古琴,1938年时就是今虞琴社的会员了,可能现在画界、琴界的人都不清楚了。
以前王世襄先生来上海住过我家,他一进门就向我父亲要菜篮子,说是要去菜场买豆苗,因为他在北京吃不到。过了两天他又去苏州弄回来一张明代的破凳子,还拿出他养的蝈蝈给我看,又给我讲为什么狗要断尾削耳。他跟父亲讲一口南浔话,当时我觉得奇怪,后来听父亲说了,才知道王世襄的母亲是南浔金家的大小姐。王先生是一个学者顽主,玩出了学问。
这样说来,您家里其实等于一个“据点”或者说是沙龙。您家里人和这些朋友平时都是怎么聚会的呢?
樊愉:你看张子谦先生的《操缦琐记》,里面似乎记录的都是琴人们的“吃喝玩乐”,不是你到我家,就是我去你家,当年都在家里聚会。现在那样的情形很少见了。


张子谦、樊伯炎琴箫合奏,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文艺会堂。
“文革”之前,今虞琴社主要在文艺会堂聚会,“文革”后有两个据点,一个是张子谦家,一个就是我家。还有,大概在八十年代以后,每周日上午雷打不动地会有一批老先生来我父亲这里聚会,一直到中午菜各自散去。因为常是欢笑连连,所以我父亲就起了个“笑笑楼”的斋名。来的大多是曲界和画界的朋友。像倪传钺老师,孙女是由他带的,聚会的时候哪怕带着孙女他也要来。再有是郑传鉴老师,他说话时的动作、眼神就像是在舞台上,这个很难形容,真是非常有趣。平时家里来往的人很多,甚至于有些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比如之前我看了白谦慎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他以前也来我家作过客。
现在关于五六十年代的回忆多了起来,但我知道的,和现在一些书里的记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现在对我母亲的了解,大多从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里面来。其实当年陈巨来和我母亲关系还不错,以前的画院在汾阳路,我们家住在新乐路东湖路口上,陈巨来住在富民路靠近延安路那里,他们上下班是同路。陈巨来老是讲些乱七八糟、道听途说的事,可能这和他的个性有关,吴湖帆不是就说过么,他爱听陈巨来讲那些家长里短的八卦,当作一种消遣。我觉得,《安持人物琐忆》这本书前面应该有人写篇导读,不要让读者误以为他讲的都是信史。
我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叫做许培鑫的,他当年和陈巨来是同室狱友,后拜陈巨来为师学篆刻,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叫做《我和老师陈巨来》。我认为这种叙述是比较准确的,能还原真实情况。不像现在好多人写到自己的老师,往往会失去历史原貌,一味吹捧,主要这样也能给自己增光。陈巨来可能不知道,我母亲受到的最大打击,其中就有一件事情就和他有关。当时要我母亲供认陈巨来的“反革命言行”,她就是不供认,说自己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陈巨来的被捕入狱与我母亲最终走上绝路不无关系。
现在不少人呼吁,说昆曲、古琴这些传统艺术要注意吸引年轻人,作为在传统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不知您怎么看?
樊愉: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有个年纪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到了一定的年纪,兴趣就来了。前不久我看一篇田青先生讲有关“非遗”和昆曲的文章,有年轻人问他,昆曲这么好,青年人不喜欢,该怎么办。他回答说,听不懂没关系,等你年纪大了自然就会喜欢的,“昆曲等了你六百年,不在乎再等你三十年”。这很有道理。你看我现在听的和喜欢的一些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要听的,但是我小时候从老一辈人那里知道了这些,他们沉浸其中,喜欢得不得了。等我到了五六十岁,确实也就开始沉迷起来了。
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弹古琴,就又是焚香,又是品茶,弄得仪式感很重,反把原本的“雅”弄成了“俗”。我从四五岁开始看老先生弹琴,从来没见过他们这样。以前的老先生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些形式,雅是放在心里面的。就像我父亲常跟我说,姚丙炎先生弹的琴最雅,可姚先生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古琴弹得如何雅。所谓的“雅”是让人感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