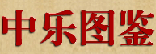恳请作曲家:千万别把江南丝竹写“死”了——采访资深江南丝竹玩家陆勤康(二)
受访者:陆勤康(上海资深江南丝竹玩家) 访问者:陈书明(《中乐图鉴》特约编辑) 摄 影:沈正国 访问日期:2017年7月18日


倾听“民声”——闵惠芬说“我们是组合家具你们是老红木家具” 陆:你说到“正当防卫”,其实这种在白相(玩)江南丝竹的时候,被初学者破坏“玩兴”的事,还真是小事。我现在担心的是纯正的江南丝竹被破坏的大事,这倒是更需要防卫的。 访:破坏江南丝竹? 陆:哦,说破坏也不贴切,也许可以算是好心办坏事吧。 访:这个从何谈起呢? 陆:这大概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那个时候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全国许多音乐专业院校和院团,纷纷举办了江南丝竹演奏比赛。 访:比赛?江南丝竹不是民间玩玩的吗?这个也可以比赛?那就是比赛的话也应该是一种民间活动啊?为什么要专业音乐院团来嘎一脚(插一脚)? 陆:你这个话真是问得我感慨万千。专业院团热衷这件事,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响应国家弘扬传统文化的号召,江南丝竹毕竟是历史悠久的一种传统音乐品种,通过比赛可以产生影响,产生宣传效应,当然也可以产生政绩对吧。 访:这倒是可以理解。其次呢? 陆:那就是这些专业院校对我们刚才聊的江南丝竹的这种民间音乐的形成和玩法,这个音乐品种的本质属性没有作深入的解读,可能觉得江南丝竹就是江南味道的民乐合奏,只不过有不少传统曲目流传下来而已。 访:但是这些流传下来的曲目是怎么玩法的,他们也许并不清楚。 陆:我想是这样的。否则他们怎么还会规定比赛一定要有新创作的曲目,这些曲目从乐队编制到创作理念,完全就是民乐合奏的那一套,只不过采用了一些江南丝竹或者说江南风格的音乐元素而已。 访:哦,这个大概就和你刚才说的丝竹乐差不多吧。 陆:是的。但问题是后来这些创作的作品,都被称为了“新江南丝竹”。使用这个名称那就是个原则性问题了。 访:哎,好像是哪里有点不对头。陆老师你说说看。 陆:首先,江南丝竹作为一个百年流传的民间音乐品种,它的名称也是在发展中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音乐文化符号。2006年江南丝竹被批准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就是说江南丝竹成为了一种文化遗产的专称。那么就像有的老师质疑的,难道遗产还有新遗产、老遗产的说法吗?好比国外的交响乐,也没有新旧之分,最多也就是古典的、浪漫的说法。前几年还出现过“新民乐”的说法,也是吃不开(流传不开)。 访:好像有这么回事,有点印象。那么第二点呢? 陆:第二点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问题。所谓新江南丝竹从作曲到演奏,它的形成方式和表现方式,它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都是民乐合奏的概念和模式,还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供人欣赏的音乐作品。而江南丝竹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玩为主。就像有的老师发给我的微信说:“以前常听父亲说‘白相(玩)江南丝竹’。就是这个玩字,体现了江南丝竹之精髓和含义。要真正玩出江南丝竹之境界,很多专业人士还不懂。”就是说江南丝竹的玩家也好观众也好,更注重享受的是这种“每遍玩的味道都不一样”的创作过程的审美体验。所以简单说起来,江南丝竹和所谓的新江南丝竹,是两种音乐活动理念、两种音乐审美体验的音乐表现形式,不存在新旧的传承关系。所以说我们许多的专家学者对保护江南丝竹这个非遗文化都有共识,但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国家要保护的是哪一种江南丝竹,什么样的江南丝竹。 访: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个道理。还有第三点吗? 陆:第三点就是这种新江南丝竹的说法如果流传下去,那么会进一步危害本来就已经“濒危”的传统江南丝竹的生存。而后人就会把民乐合奏式的新江南丝竹当成传统的江南丝竹,这种误导,就会让真正的江南丝竹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声无息地消失。你说,这是不是需要“正当防卫”的大事。 访:就是啊。我们成天喊着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文化,抢救文化遗产,其实不知不觉就在这种弘扬、保护、抢救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破坏了传统文化。 陆: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江南丝竹身上,案例多得是,就像赵丽蓉、巩汉林的小品那样,搞个什么rap唱法的“新评剧”。 访:对啊,这种也算是“创新式的破坏”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对传统文化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为了继承和发展,而是为了市场而标新立异罢了。 陆:我们先不说动机和目的,我们只是说“新江南丝竹”这种说法的客观存在,会对传统的、纯粹的江南丝竹传承造成强大的冲击,甚至是一种灭顶之灾。 访:那你们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为真正的江南丝竹发声音。 陆:我们没有大的舞台可以站,没有发声的地方,没有话语权。因为我们是玩民间音乐的“民间派”,不是“院团系”。他们把江南丝竹贴上了专业的标签,所以“院团系”就有了绝对的评判权。 访:这个讲法是不讲道理的。江南丝竹本来就是民间音乐,你说谁玩得最正宗?当然是“民间派”,“民间派”讲民间音乐天经地义。你“院团系”要么为了比赛,要么为了特殊需要,一年才搞几次江南丝竹,而且还是民乐合奏模式的新江南丝竹,也就是说你都没有弄明白江南丝竹是啥,你凭啥拥有话语权和评判权?而像你们这种“民间派”几乎是天天泡在原汁原味的江南丝竹里面,才可以说是拥有天然的、无可争议的发言权。如果换个说法,就是在玩江南丝竹这件事情上,“民间派”应该是专业的,“院团系”才是业余的。 陆:人家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的,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些民间团体即使搞江南丝竹再专业,也是玩玩的,人家就是再业余,也是搞研究的。 访:问题是他没有研究呀。毛主席都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陆:这倒也是,我玩江南丝竹将近60年,就像你刚才说的天天泡在江南丝竹里,调查得也算够深入了。从小我父亲就带我出来玩,在一批江南丝竹大家的团队里玩。他们都很喜欢我,我学会一曲他们就让我上手玩。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我玩的时候都是和高手过招。在乐队里既感受到了别人的玩法,也检验了我的玩法。而在看别人玩的时候,我又可以仔细品味这些大家各具特色的技法,以及这些技法带来的江南丝竹特有的味道。 访:比如说呢? 陆:比如说音律方面,那时像笛子之类的乐器都是平均孔,不像现在的定音孔,所以在演奏时需要通过演奏者在按孔吹奏过程中进行调整,去往扬琴等十二平均律的音律方向去靠,所以出来的效果既不是纯粹的十二平均律,也不是完全的五声音阶。 访:那就是别有风味的江南丝竹音阶了。 陆:就是这个意思呀。现在的人都是在西方十二平均律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是听不惯这种音律的。现在搞江南丝竹的大多是走十二平均律的路子,这也是今天的音乐审美的选择,可以理解,但就是缺少一些过去的那种“似准非准”的,那种“原生态”的江南丝竹味道。我还清楚地记得有的老先生拉胡琴,除了食指用指尖按弦之外其余都是用指肚按弦的。 访:对了。我记得有一位玩过江南丝竹的民族乐团老师对我说过,指肚揉弦和指尖揉弦出来的音色是不一样的。 陆:当然不一样。所以说民间音乐里面,无论是音律、技法、音色等演奏方式和演奏技巧,都有着充分的丰富性和自由性。它没有“院团系”各种规范套路的“约束”,所以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怎么有味怎么尽兴就怎么玩。 访:哎?那么那些“院团系”知道你们这么玩码?他们来玩过吗? 陆:来过,很多民乐界的老前辈都来玩过,像陈永碌、许光毅、王乙、林石城、何冰、刘德海、闵惠芬、俞逊发等。其实这些“院团系”大家在建国初到文革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玩过江南丝竹,都为新时代的江南丝竹繁荣做出过贡献。 访:那他们会下场来玩一曲吗? 陆:有时候会坐上来助助兴,但大多是来听听的。像闵惠芬啊、俞逊发啊这些演奏大家都会很客气地说,我们是来学习的。用闵惠芬的话来说,玩江南丝竹,我们是组合家具,你们才是老红木家具。 访:这个话精辟,也形象。他们可不是用总谱组合出来的音乐嘛,你们玩的才是像百年老红木那样原汁原味的江南丝竹。这个话其实也可以成为一种论据,那就是应该还江南丝竹的话语权给民间。 陆:其实说起来,以前很多“院团系”民乐大家、民乐前辈,最初也是从民间走进专业音乐院团的,像卫仲乐,金祖礼,孙裕德,刘德海等大师级的人物,都是非常熟悉和热爱民间音乐。他们虽然是置身于专业院团的大家,但他们的双腿是深深地扎根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才会有如此的艺术成就。而现在有些“院团系”的音乐家,虽然他们最初也是从民间考入专业院团,成为了“院团系”,但可能是因为天天泡在了西方的音乐理论当中,就逐渐忘记了江南丝竹这种民间音乐该怎么玩了。 访:该怎么玩?就应该告诉他们不忘初心。我听说现在长三角不是经常搞什么江南丝竹比赛吗?好像台湾、新加坡什么都来的。那就让他们不要老是比什么音准啊、节奏啊,表现力什么的,要比的应该就是真正江南丝竹的文化特点、它精华的表现方式什么的。比如就规定每个曲子奏三遍,看谁玩得味道浓。哪个队让台下观众打瞌睡了就淘汰。哈哈…… 陆:哈哈……,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好在已经有不少专业音乐院团的专家老师,对江南丝竹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他们都认同了我们刚才聊的观点。你看这几个微信……这个,“江南丝竹不是凭音准,节奏,演奏附号能拉好的,……一些专业演奏者们从音准等方面可以说问题不大,但却不像江南丝竹,他们不能领会,也说不出什么叫江南丝竹” 访:对了。这就像让音乐学院的学生去沪剧团拉主胡也出不了那个味一样。 陆:你看这个老师说的“我们要发展,这是共识。如何发展,这是症结。专业人士应和民间有识之士结合,共商发展。自古以来的‘士在民间’同样存于江南丝竹,因而,还话语权给民间,这是发展之必须。” 访:这个老师思路清爽。 陆:应该说专业音乐老师当中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对江南丝竹进行认真的解读和品鉴。前一阵中国音乐学的大家乔建中先生来上海,专门和我聊了六七个小时的江南丝竹。你看看,这是他发给我的微信:“陆老师,微信收悉,谢谢你的坦诚之见,鉴于您本人有数十年‘江南丝竹’的传承经历和实际感受,您作为这种地域音乐文化瑰宝的‘持有者’,您对于她的学术定位和自身的艺术规范的见解,我是完全赞同的。……您现在提出这些‘民乐作品’不可与传统‘江南丝竹’同日而语,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请您允许我认真想想,再和您讨论……”


忧“新江南丝竹”——别让西洋作曲法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没了 访:“乔老爷”能够认可你的江南丝竹理念,这还是对传统的、纯正的江南丝竹一个很有分量的肯定。 陆:说实话,我真的是担心江南丝竹会被所谓的新江南丝竹替代,而把老祖宗正统的好东西弄没了,将来小朋友只知道那种民乐合奏式的东西就是江南丝竹了。 访:这个倒真是个严重的问题。看来传承江南丝竹也得从娃娃抓起。 陆:就是啊。我现在对培训班的小朋友就是一直在灌输江南丝竹的“活”思想。 访:你是怎么教他们玩的。 陆:比方说,我会写一条简单的旋律在黑板上,让小朋友回去,根据自己玩的乐器特点,用江南丝竹各种各样的套路每个人写五条变奏的旋律。第二天我会挑选一些写在黑板上,然后进行分析,也让小朋友自己思考,你二胡用这条旋律的时候,我琵琶怎么弹;你琵琶用这条旋律的时候我箫怎么吹、扬琴怎么敲……你想想这个可以组合出来多少种效果。 访:对,这个好。这比那种乐队排练时候大家按照自己的声部,去看着定死的分谱等拍子要丰富得多了。 陆:那当然,我就是培养他们一种即兴的、自由的、玩的概念。 访:这种培训方法倒是特别的。其实中国传统音乐在口传心授的传承过程中,必定就会带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就是到了减字谱、工尺谱的时代,也是那种“似有框架又无约束”的“写意”性的乐谱。 陆:对,这个和江南丝竹的发展是异曲同工的。我经常讲江南丝竹就像一条河,“母调”就是河道,各种各样的变奏就是河水,它可以在千回百转的河道里欢蹦乱跳、自由自在地走得老远老远。 访:而且一路上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融入各种各样的细流,让河面更为宽阔,也就是更加丰富了江南丝竹的玩法。 陆:是啊,你仔细想想,江南丝竹其实也是融合了许多地方和民族的很多种音乐元素和技法。你比如爵士乐那种即兴的元素,还有复调、对位的手法等等,都是会随时随地、灵活多变地出现的。 访:但是都玩出了中国江南的味道。 陆:对,关键就是江南的味道。我记得1986年英国女王访华来上海的时候,上面觉得应该用最中国、最传统、最民间的文化来接待,到了上海嘛,江南丝竹当然是最上海的了,所以审查了很多团队的节目。好像有上海民族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歌剧院、上海音乐学院等等,最后是选了阿拉(我们)这支队伍。 访:哦?那时蛮有意思的。你觉得选了你们这只业余的队伍是出于哪些原因呐。 陆:我想,首先要从江南丝竹里的一些音乐特点、音乐元素来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江南丝竹里早就有爵士乐的即兴元素,也有复调、对位等技法的运用。这些音乐技法和手法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会对音乐产生一种亲切感。而他们最想听的是,你们中国人是怎么玩这些外国东西的。那么在审查的过程中,那些专业院团的乐队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江南丝竹,是那种已经让作曲家写死了,而且经过认真雕琢的、已经民乐合奏化的江南丝竹,已经找不少即兴的元素了。而我们上去演奏依然是一种玩的状态,是一种自由的、即兴地玩对位、玩复调的状态,可以给外国人一种“似与非似”之间的审美享受,是纯民间、纯上海的一种民间音乐文化。我想这就是选择我们这支乐队的原因吧。而且,从这次接待之后,我们接待过几十个国家的元首政要,也接受了数百家各类媒体的采访,还出访了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甚至还有许多境外搞民族音乐的人专程来访和我们交流。他们都对这种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非常感兴趣,觉得江南丝竹非常中国,可以玩出非常高深的文化境界。 访:这个案例其实很有典型性的。我们可以想得发散一些,就像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在1989年那篇《危机中的抉择》谈到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传统音乐都在致力于走一条融合西洋音乐技法、音乐思维的改良道路。从几十年走下来的情况看,也许可以说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已经被西洋音乐体系给替代了。 陆:就是,你想想,现在学校还有教古代律吕音律的吗,还有教减字谱、工尺谱的吗?有多少人知道相和歌、知道大唐乐舞、知道诸宫调和明清说唱。中国的音乐教育几乎都是五线谱的天下了。 访:所以民族乐器改良的老前辈张子锐早就说过,百年来中国音乐不教中国乐理是最大的失误。 陆:就是啊,不教中国的,那就像周教授说的走一条用西乐改造中乐的道路。其结果如何呐?无非就是按照西洋作曲的套路,来改造、同化、洋化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器乐。也许我的说法不恰当,那几个审查未通过的“院团系”乐队就是这种改造、同化的结果。然后他们还要用这种被改造的模式,来继续改造江南丝竹这样的民间音乐。可其实你看,那种爵士乐式的即兴、那种复调、对位等等技法,我们早就融合进江南丝竹了。我们可以融合,是将融合进来的东西为我所用,把它消化在我们的特色里,而不是被它改造。 访:你说的对,民族音乐当中在器乐方面的“洋为中用”改造尤为典型。比如在建国初期的“激情岁月”中,就开始仿照西洋交响乐队编制,来追求大型民乐合奏,这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改良理念。 陆:对。其实这是对西方交响音乐,对中国民族音乐、民族器乐以及不同的乐器文明,在文化、历史层面缺少认真的解读所导致的结果。 访:可以请老师举例说明吗? 陆:你比如我们的江南丝竹,为什么三五件乐器,或者最多十几件乐器,都是“单打一”的、几乎每种乐器都只有一件组合在一起玩。 访:哎?好像是这样的。为什么呐? 陆:因为你知道,中国传统乐器单个的音色都非常优美,但每种乐器的音色又非常有个性。所以说,就中国乐器现在的声学品质状态,这种“单打一”的组合,应该是集中了中国乐器音色优美的优点;而几十人的、同品种多件组合的大型乐队,几乎就是集中了个性强的缺点。所以我一直觉得,西洋乐队的乐器大多一组一组地、音色协调统一地发展起来的,比较利于在大型乐队中进行交响,而中国乐器这种“个性美”的特点,最适合在小型乐队里进行交流。请注意,一个是交响,一个是交流。 访:哎,这个说法好像挺有道理的。像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什么的,应该就是这种符合中国乐器特色的器乐组合。 陆:对,没错。 访:看来这个音乐历史的解读,音乐文化的底蕴,对于写音乐的、玩音乐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陆:对,你说出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民族音乐领域可能重视技术、技巧的程度,要远远高于重视文化的程度。这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他们除了自己学的音乐专业,在其他方面的文化积累是非常有限的。你想嘛,五六十年代那一代人考音乐学院,应该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会对文化程度有什么要求,说不定会唱个歌就能考进去。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专业音乐院团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也只有230分左右,那可能就是初中、高中的程度吧。关键是他们还没有前辈们在生活中对传统文化浸润的积累,那就只剩下了技巧训练、炫技的追求。 访:要这样说,其实不管是写音乐的,玩音乐的,或者是玩江南丝竹的,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撑,都是玩不出高境界的。 陆:当然了。而且不仅如此,没有文化底蕴还会作出许多“没有文化”,或者说“误读文化”的事,就比如用西洋作曲方式来创作江南丝竹,那个东西我说就像是无纺织布,大多数都是化学的东西了。 访:是啊,这就好比是用钢筋水泥修补长城,用玻璃幕墙改造故宫,然后再冠以“新长城”、“新故宫”的名称,这样就太可怕的。 陆:如果这样改造、这样冠名的话,对后代来说这是犯罪也不为过。 访:对呀。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冠名了。这些作曲家、音乐专家们轻易地就把那种西洋作曲方式创作的,那种民乐合奏模式的,有一点江南风格、江南丝竹元素的器乐组合,称为了“新江南丝竹”,给戴上了传统的、民间的帽子,这要是流传下去,不仅对后代是一种误导,更是将真正的江南丝竹至于死地。这个往远了说,是愧对子孙后代。而这么辛辛苦苦地写曲,也在辛辛苦苦地毁灭着“非遗”;往近了说,这样的冠名对现在的江南丝竹生存环境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陆:是啊,现在虽然玩江南丝竹的人不少,而且就像有的老师说的,这里面有很多人在用自己对江南丝竹的那份守望,那份热爱,在不经意间巧妙地对它进行了发展,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尽到一份责任,是一份功绩。但是话说回来,现在“院团系”也好,“民间派”也好,真正能把纯正的江南丝竹玩到高境界的,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几个人了。 访:要不然,你们就自己关起门来玩,自然地生长,慢慢地星火燎原,也别让“院团系”来研究了,省得老是弄出个什么“新江南丝竹”,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个“三代江南丝竹”什么的。 陆:这个我倒不是这么想的。我是希望“院团系”的那些专业的作曲家、音乐家,能够沉下心来关注和研究江南丝竹,实实在在把江南丝竹音乐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提升,进而推动它更加“活态”地发展。 访:这倒也对。现在从实践到理论、从学院到民间,玩江南丝竹的不少,但能够专心致志来研究江南丝竹的很少。 陆:所以啊,说起来研究得不多,但写出来的作品倒是不少,只可惜都写得太满,都写死了,写得我们都没法玩了。 访:对呀,就像刚才说的,江南丝竹不是大型乐队的交响,没有24行总谱会乱的。江南丝竹是多种丝竹乐器“单打一”的组合交流,不用定得那么死,给个“主题”自由讨论、自由发挥就是了。 陆:说得没错,既然是在这个小型的器乐组合里进行交流,你就应该给它们每件乐器一个自由发言的权利,只需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也就是“母调”就可以了。 访:就是呀。你要是用西洋作曲法来写个总谱,那就等于给每件乐器写好了“发言稿”,那也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那么江南丝竹也就给“写死”了。 陆:所以我说作曲家们要是写真正的江南丝竹,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写一个基础的“母调”旋律就可以了。最多写一个最简单的配器,一个极其压缩的缩略总谱,给一些主要乐器写一个“发言提纲”就可以了,这样才能给我们留足自由变奏、即兴发挥的空间。 访:对,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流传下去,将来江南丝竹可以从“八大曲”变成“十八大曲”、“二十八大曲” 陆:但愿如此。好了,我儿子来短信了,我要去机场接他了。阿拉(我们)约时间再聊。我有交关(许多)想法、交关故事好讲了。 访:那最好了,谢谢陆老师!就怕你太忙。那我搭你的车走吧,正好路过我家。 陆:那正好呀。走,车在楼下。 访:……哟,大奔嘛。我又想到刚刚讲的,30年代白相(玩)江南丝竹的都是有钱的,现在还是这样。 陆:我也算不上什么有钱的,不过我倒真的不是靠玩江南丝竹活着的,但我希望江南丝竹能好好活着。来,抬抬手戴好保险带。 访:好,那就让作曲家们也高抬贵手,给玩江南丝竹的也上个“自由险”。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