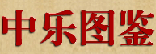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寻找李少春”
编者的话
日前在朋友圈,看见了微信公众号“寻找李少春”发布的京剧评论文章“为京剧号脉:花钱越多,艺术的含金量越低”一文,颇觉值得一读。文中所列当下京剧界各种现象,有许多在民乐界也多有比照、“共鸣”之例。文章举例、梳理、剖析、“开方”面面具到,观点鲜明、一针见血直抵病灶,可谓是一篇直抒胸臆、“直言进谏”的“檄文”。这篇写京剧的文中诸多“捅破窗户纸”的观点、观念,对民乐界而言同样不无借鉴,具有警醒甚至“幡然猛醒”的作用。
文章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对于京剧文化和民族音乐文化至诚的守望者们来说,这一番诤言很有分享和思量的价值。
本篇各段配有“编者刍议”, 并由编者自网络辑得相关配图,特此感谢!
为京剧号脉(之一)——对主演中心制的忽视
为什么几十年难出一个新流派?
为什么十几年来没有一段流行唱腔?
为什么百万元难排一出好戏?
为什么得奖越多的剧目,剧场的上座率越低?
这些问题若找不到答案,京剧艺术就难以走向市场,就会影响京剧艺术按其自身规律健康发展。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对主演中心制,也就是对京剧“明星制”的忽视。
曾经编导过京剧《赵氏孤儿》、《海瑞罢官》和《望江亭》等经典作品的王雁先生说:“我虽身为编导,但是我要强调,话剧看导演,电影看剧本,京剧看演员。”此言一出,全场为之鼓掌。王老说:“写京剧剧本,就是要给演员写,要写出演员的特色。导演要导出演员的风格,尊重演员的艺术个性。因为观众要看的是演员,是名角。”其实,这正是京剧艺术家争奇斗艳,流派林立的重要因素。正由于我们坚持为演员写戏,为演员编唱腔,为演员导戏,都是以主演为中心进行标新立异,开展艺术创造,李释戡和齐如山为梅兰芳写出的《霸王别姬》才成为梅派的世纪经典;翁偶虹为程砚秋写出的《锁麟囊》才百演不衰;陈水钟为荀慧生写出的《红娘》才成为传世之作;吴幻荪为马连良写出的《十老安刘》才演出了马派的风格特色……这才有了各自的艺术个性,才有了各自的流派剧目,才有了流派。正是因为编剧王雁和导演郑亦秋了解并研究了马、谭、张、裘四大流派特色,才量体裁衣,为马、谭、张、裘编导出展示四派风格的合作剧目《赵氏孤儿》。
相反,如果以剧本和导演为中心,演员的艺术个性被抹杀,艺术特色被淹没,艺术水准被限制,梅兰芳何以为梅兰芳?马连良何以为马连良?如果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都唱一位作曲家的一种风格的唱腔,又何来梅、尚、程、荀?一位没有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的演员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又如何号召观众呢?因此,近年的演员除了打起前人的旗号,跟在前人的流派后面跑,又怎么能创造自己的风格流派呢?君若不信,那么请问:哪位导演能设计出梅兰芳的“捧印”,取代梅兰芳几十年的艺术积累?哪位唱腔设计能编创出张君秋的唱腔?哪位编导能编导出李少春的《野猪林》?所幸当时的京剧没有导演中心制,否则,梅兰芳的“捧印”必然面目全非;程砚秋的“程腔”自然没有“程”的味道;当年有人要马连良去改演周信芳的麒派《宋士杰》恐怕就不是京剧史上的笑话,而要变成残酷的现实了,“南麒北马”就真要“非驴非马”了,足见发挥和保护演员的创造性和艺术个性是何等重要了。
既然京剧是演员的艺术,看京剧就要看名角。都是《四郎探母》,上座率也有高有低;都是国家剧院,演出也有好有坏。为什么某位县剧团的名演员一调动工作,那个县京剧团就没有了?为什么某位名角逝世,一个省剧团就再也不能进北京了?为什么一个演员告病假,一出好戏就没人看了?一言以蔽之,观众在主演、导演、剧本面前,首选只能是主演。只有推行明星制,大树特树“角”的权威,京剧才能上座,新的流派才能产生。


(民国早期京剧戏票)
编者刍议:
●从上述文意可见,观众看戏最看重的是演员以唱为主的表演,而唱腔也是体现艺术流派的最重要的特征。
●京剧在流派纷呈的盛世,同一出戏可能会有不同流派的演绎,比如梅派、程派都有《玉堂春》,都是叫得响的流派戏。而因为两版《玉堂春》都是为流派艺术量身定做,所以虽然故事内容相同而流派风格依然“泾渭分明”。(当然,也有些流派艺术家在“同戏不同派”的情况下,感觉别的流派效果更好,于是自行“歇演让戏”,体现了高贵的戏德。)为演员写戏,实际也就是为艺术流派写戏,尤其是为流派编腔。这其中当然也会考虑演员的嗓音条件及表演特点等等。
●而以民歌来说,虽然“歌保人”的情况不少,但像施光南与关牧村这种“量体裁衣”的模式也时有所见。这种全力体现出演员艺术鲜明特色的作品,大多可以成功的流传,似乎与文中观点“不谋而合”。
●现代民族器乐作品的演绎在旋律、配器、奏法等方面比较讲究规范和整齐划一,当然不同的乐队指挥或独奏演员也会在作品乐谱的“框架”中进行一些“有限”的、不同风格音乐处理方面的“润色”。作为演奏者来说,虽然多有代表作来彰显自己的音乐艺术追求,但囿于标准的乐谱,几乎不太可能形成特色鲜明的流派。即使是流派纷呈的京剧,如果将唱腔“标准化”,恐怕也是难以产生各种流派的。所以对很多民乐演奏家的评价多是“细腻深沉”或“热情豪迈”等演奏特点方面的形容,若论艺术流派单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传统民间器乐流派比如浙江筝派、山东筝派等,那都是从旋法、奏法、声韵以及代表人物、流传范围、作品积累、艺理论述等各方面都是“自成一体”方成流派的。
●前辈民歌演唱家不说流派纷呈,至少也是名家众多,在嗓音特点、演唱风格、作品样式等方面都是独树一帜。比如郭兰英、王昆、马玉涛、胡松华、郭颂、李双江、蒋大为、阎维文等等,艺术特色都有很高的辨识度,而且也有众多拥趸。如今听民歌很难有以前那些名家的辨识度,很多歌者一开口多是“学院派”的味。虽然他们也有很多歌迷,但这些歌迷往往是“追人”重于“追歌”、“品歌”。
为京剧号脉(之二)——花钱越多,艺术的含金量越低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大制作带来艺术的退化,只见花架子,不见真功夫,花钱越多,噱头越多,京剧艺术的含金量越少。
对话剧和京剧做过认真研究的戏剧大师焦菊隐曾非常明确地说:“话剧是布景里面出表演,京剧是表演里面出布景。”我们也向国外说我们的《三岔口》是如何通过演员的表演在几千瓦的灯光下制造出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是如何通过演员的表演和一只船桨在空旷的舞台上表现出那激流勇进的一叶小舟;是如何通过演员的表演使京剧的舞台上时空变幻自如。因为京剧的特色之一就是她的写意性和虚拟性。所以京剧以她不同于话剧表演的独特风格屹立于世界文艺舞台;所以曾经在京剧中使用过布景的梅兰芳以他的亲身教训一再嘱咐我们说,用布景不但没有好处,还会限制我们的表演。所以裘盛戎在排现代戏《雪花飘》时说:“你们又是风,又是雪,还要我们演员干什么?”所以,《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忆十八》是用什么布景都无法解决这十八里路瞬息变化的风景线,而我们通过演员的表演却巧妙生动地描绘出这一路风光,而且情景交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确一点:戏剧是“情为主,景为客”,观众看的是鲜活的艺术形象;观众不是来看独木桥,而是来看梁祝二人过桥时怎么触景生情;观众不是来看风雪,而是要看老人冒着风雪给人送电话的那种精神。
然而近年来,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排演大戏,时兴大布景,大制作。结果,白天演黑夜不再用虚拟,写意手法,现代的灯光科技似乎更新鲜,更省事;有真船上台,机关操纵,《秋江》的表演似乎也过时了;更有台上搭台,中心表演区充满了台阶,动不动就要演员上下台阶,甚至真楼梯上台。似乎演员的圆场功也不用练了,虚拟化的上下楼梯表演更不用演员下功夫学习了。要知道,京剧艺术必须“有声必歌,逢动必舞”,而且其规范就是一个字:圆。如今的舞台上,圆场寸步难行,怎么舞?怎么圆?再加上高级音响或者先期录音,对口型,不用费劲就可以“满宫满调”,不用出音,就可以获得“掌声雷动”,如此发展下去,请别人代替录音,不是更能精彩吗?似乎嗓子也不用练了,唱腔也不用学了,来点双簧就全有了。曾有报道说,某大剧院排演一出《宝莲灯》,唱、念、做、打、舞,一字不提。只说他们与某科技公司“联手合作”,一只“宝莲灯”就花费了几十万元,此灯可以通过电脑遥控在观众席中飘来飘去。真不知这个报道是让观众去看灯呢?还是去看戏呢?如果京剧如此发展,还有什么艺术可言呢?某剧的皇帝由金殿转入后宫,这个过程本无戏可做,是应该简化处理的,由太监“一翻两翻”,喊一声“万岁摆驾后宫”就解决了,这就是我们戏曲的高明之处。为了出新意,竟然采用了“转台”,不仅劳民伤财,也是画蛇添足。好像只有大制作,京剧才能振兴,才能改革出新。钱都花在这上面了,京剧的表演艺术的价值又在那里呢?


(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场景之一)
编者刍议:
●文中的很多例证,回答了“为什么花钱越多,艺术含金量越低”这个问题,因为多花的钱都是用来破坏京剧的写意性、虚拟性表演,破坏“四功五法”等京剧艺术属性和根基的,所以花那么多钱,只是“画蛇添足”地装修了京剧的“盒”,而破坏了京剧的“核”。就像文中所言,是让观众去看几十万的灯,还是去看戏。久而久之,京剧演员可能既废了传统的功,又不知该怎么练时尚的功。而观众光顾着看布景分散了心神,也难以专注于什么唱段,更不用说流传了。
●民族音乐舞台上的声光电同样光芒四射,让观众目不暇接。以此来渲染乐曲、歌曲似乎成为了博得剧场效果的捷径。更有甚者,整台的音乐会被演化成了舞美大制作的展览,演奏家还需要“不务正业”地朗诵、表演,而器乐作品则成为了背景音乐。这种难以复制的场面湮没了音乐,又何来流传。只有让观众在“干干净净”的剧场安安静静地听听歌、品品曲,那才能让作品“真实而完美”地展现,进而生成真正的艺术品鉴。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艺术之“核”,比如京剧艺术的“牛鼻子”就是京剧音乐,就是唱腔。百多年的传承最倚重的也是唱腔。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民族器乐、声乐之“核”就是优美的旋律,年年代代流传的也都是可以朗朗上口的旋律,而不是那些“奏得出,唱不出”的无调性音乐。要让这些艺术之“核”不断发光,靠的是不断打磨、不断积累的艺术创作,而不是靠金钱能堆出来的。
为京剧号脉(之三)——京剧的话剧化
在近十几年排演的大部分新戏中,最罕见的是武戏;最不讲究的是唱念做打的基本功;最重要的标志是“大胆打破传统的模式”;劳民伤财最多的是灯光布景;最终目的是获奖;最后的结果是内部演出两场,或者拿出人民的血汗钱慷慨赠票,凑足场次,还美其名曰“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其实,没有票房价值,又哪来观众?又哪来社会效益?而这种种后果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剧的话剧化。
应该说,目前不少新排剧目的作者是话剧的,导演是话剧的,舞美是话剧的。他们不但对京剧一窍不通,而且对京剧充满蔑视和反感。有一位导演说,我就喜欢黄梅戏,没有那么多传统的程式,容易改造。难道一个剧种的历史短,不成熟就是优点;历史长,很成熟就是麻烦吗?这正好说明她根本不是来排京剧,也不是来排黄梅戏的,而是要“改造”京剧,要排话剧化的京剧或者黄梅戏。因此,他们的剧本与京剧的表演完全脱节;这样的导演只能要求演员转向写实性的表演;充其量也就是话剧加唱。例如京剧剧本必须给演员的表演留有余地,可以用动作身段和舞蹈特技来表现情感和剧情。像京剧的《花田错》,中心场就是“买画”和“做鞋”,其生动所在都不在台词上。你不懂京剧的四功五法,不懂京剧那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法,怎么“写”的出来?又怎么“导”的出来?结果都用台词表示,这能是京剧吗?至于武戏《挑华车》和《三岔口》都是公认的京剧经典,但是两出戏的剧本都不过两三页,要让话剧演员读剧本是无法读通的。甚至那出红遍国际舞台的《雁荡山》却是一句台词也没有。你不认真学习京剧程式的运用法则,不认真研究京剧的艺术特征,怎么能写京剧,排京剧,改造京剧呢?我们讲“推陈出新”,可是你没有见过“陈”,不知道“陈”为何物,又怎么“推陈”呢?
前几年,某些戏曲学派,公然反对继承传统,提出了“断裂论”,说“现代戏剧不能从娘胎中带出一点痕迹”。目前,这种论调没有了,但是让话剧编导来编导京剧的新戏,以为只要布景好,台词好,情节好就是好戏。只要能“打破京剧行当的限制”,“打破传统的框框”,“打破京剧的程式化表演”,传统的东西越少越可以“出新意”,如此“继承传统”岂不是一句空话。好像京剧的行当、程式、规范都是那么陈腐不堪,十恶不赦。从而使京剧走向话剧的写实性表演,走向“话剧加唱”,让京剧演员也“从布景中出表演”,把整个京剧都给“打破”了,这还能叫京剧吗?想想当年,梅兰芳先生排演新戏后总要问观众:“您看像京剧吗?”李少春排出新戏后总要问:“您看哪些地方不像京剧,请您指出来。”而今天我们在北京京剧院的排演场上竟然听到一位话剧导演大喊:“你们为什么总像京剧?”可谓时过境迁,真不知京剧何罪之有?其京剧前景怎不堪忧?


(华宴——新京剧《霸王别姬》中一匹真马被拉到台下与霸王诀别)
编者刍议:
●剧团或角儿请相关的内行外援来增强“艺术实力”也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早年的齐如山之于梅兰芳、翁偶虹之于程砚秋等,由于这些文化人都是京剧的资深内行,所以对京剧的出新和品位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像现在京剧院不请名角,不请名琴师,却请来话剧导演大声指摘“你们为什么总像京剧”,就令人匪夷所思了。难道请个外援不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京剧,只是为了用话剧来消灭京剧?这不是为了“推陈出新”,因为请的外援根本不懂“陈”,这几乎是奔着“灭陈推新”而来的。这和民族乐团不请作曲家、演奏家的外援,而是请舞台导演为外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动机上看就是为了剑走偏锋地“玩花活”。
●“话剧加唱”的改造,类比在器乐方面多表现为“演奏加形体表演”,而且从偶尔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上别出心裁的拍击,逐渐演化到了演奏员互相击掌、走台步等舞台表演,生生将器乐演奏家打造成了“表演艺术家”。更为令人瞠目的是,有些器乐老师还专门打着拍子培训表演夸张的演奏动作,这种贻害无穷的本末倒置之举,实实令人担忧。
为京剧号脉(之四)——只创新不继承
京剧把唱腔放在第一位。所以看一出戏,首先要看其唱腔成功与否,凡是好的唱腔必然脍炙人口。但是近几年新戏不少,新腔更不少,却难得有唱腔流传。我以为原因有四:一是唱腔缺乏艺术个性;二是重旋律轻字韵;三是步子迈得太大,华而不实;四是旋律高亢有余,失之委婉。
我们前面提到,观众看戏看名角,就是因为名角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梅派有含蓄之美,荀派有娇媚之态,程派委婉动听,尚派柔中寓刚,观众各取所需。总是一个味儿,听了梅派又何必再去听程派呢?那么如何创造出自己的唱腔特色呢?这就要演员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和艺术风格去创造,或者要求熟悉自己的唱腔设计者从自己的条件和风格出发去创腔。张君秋先生就说,当年王瑶卿先生帮助程砚秋编《锁麟囊》的唱腔时“十分注意演唱者本人特长的发挥,为程砚秋设计唱腔就注意到程派的深沉凝练,委婉迂回的特色,为其他演员设计唱腔则又是另一种风格”。应该看到,在戏曲发展史上,成功的演员都是自己创腔。新凤霞就说:“流派的形成,主要靠演员自己创造。专唱作曲家谱曲的演员,难以形成自己的流派。”张学津所以在唱腔方面有独到之处,则与他23岁便成功自创《箭杆河边》的唱腔不无关系。目前,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京剧团都是用一位作曲家的唱腔,所以在全国性的汇演中,许多戏都是一个味道,如此发展,京剧唱腔的艺术个性就要被这种高度的“共性唱腔”所取代,不要说流派、特色形成无望,艺术家的创造意识也都被彻底阉割了。
由于某些专职作曲家忽视了戏曲“以字生腔”,“文乐一体”和四声与反切的法则,不知有字才有韵,字正才能腔圆,无法体会演员在吐字发音时的感觉,只能在设计的旋律中填字,所以,唱者,听者都感觉味同嚼蜡。其实,唱腔是语言的夸张与延伸,唱腔最高的境界是说,必须以字韵为唱腔的基础和灵魂,京剧如此,郭兰英、李谷一和邓丽君的歌曲所以经久不衰,又何尝不是如此。而重旋律,轻字韵,必然使唱腔失去灵魂,从简洁走向繁复,从唱“意”走向唱“形”。吐字发声也从四声分明和反切清晰到囫囵吞枣,有腔没字。所以不能朗朗上口,又怎么流传呢?
最让观众和演员望而生畏的还是唱腔音域偏高,有些新戏几乎每句唱腔都要翻高八度,每段唱腔都要使用嘎调,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火药味,以至很多高腔重复使用,令人不堪入耳。唱者声嘶力竭,闻者心烦意乱,岂不知,唱腔有低才有高,如果把唱腔都停留在高音区,不但失去唱腔的力度,也忽略了唱腔层层递进的基本法则。每句都用高腔,还能有高腔吗?更何况,七分为吟,八分为唱,十分为嚎,十一分就是吼了。演员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还要翻高八度,还有什么美感可言呢?
“移步不换形”是梅兰芳几十年来研究观众欣赏心理和戏曲艺术规律的经验之谈。他说:步子迈得太大,观众不习惯,要让观众在熟悉的唱腔中感到一定的新鲜感,而不能面目全非。遗憾的是大师的话是那些只想“出新”,不考虑观众接受与否的人根本听不进去的,所以一些新腔明显地脱离群众,又怎么流传呢?


(传统京剧《三岔口》在强烈的舞台灯光下虚拟的“摸黑夜战”)
编者刍议:
●传统京剧的唱腔似有“一曲多词”的特点,但每段唱又都有不同之处生成不同的韵味。这种“似与非似之间”的感觉正符合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经验之谈。从京剧发展的历史来看,京剧创新腔应该是在千锤百炼琢磨老腔的基础上灵光乍现所得,才会韵味隽永地广泛流传。
●梅兰芳在国庆十周年排演新戏《穆桂英挂帅》时,与早年“标新立异”的创新有着质的不同,不再追求“载歌载舞”,而是强调“新戏不新”,回归传统,重视京剧本体。而《穆桂英挂帅》也成为了建国后创作的、能够广泛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的佳作之一。
●民族音乐中许多成功的、广为传播的作品如《放马山歌》、《小河淌水》、《阿细跳月》等等,也是源于人们熟悉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元素提炼而成。新作只有植根于肥沃的传统文化、民间音乐土壤,才能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有京剧业内人士分析,现在的京剧人对待创新和继承有着不同的理解。京剧历史上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一座座艺术高峰,即使像梅葆玖这样的流派传人,还可以在73岁为电影《梅兰芳》配音的时候,唱出十七八岁小姑娘的甜美,现代京剧人即使常年苦练,似乎也难以达到前辈的“坐标”。但创新就没有了艺术参照,“标新立异”自然就容易“成功”获奖。这就如同现在有些民乐作曲经常将前辈的经典作品视为“小儿科”,实则现在未必能写出当年那样优美而广泛流传的旋律,能达到当年的艺术高度。
为京剧号脉(之五)——惟新主义作怪
近年来京剧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剧团排新戏,票房唱老戏;老戏国外热,新戏获奖忙。不但评奖必须是新戏,评“梅花奖”的演员也必须有新戏,评价一个剧团,一个演员,也要看有没有新戏。在他们眼中余叔岩、孟小冬、金少山这样红极一时的艺术大师没有新戏便不值一提。更有甚者,他们排演的新戏必须面目全新,不能有一点传统的味道。总之,“新”成了某些人检验艺术的惟一标准。然而,我们面临的京剧市场恰恰相反,观众是非名角不看,非好戏不看。纪念徽班进京200年的大汇演,票房价值最高的是关肃霜的那场拿手折子戏;在第二届京剧节上,最抢手的戏票是唱了100多年的《四郎探母》。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艺术标准是真善美与假恶丑。江泽民同志提出“振兴京剧和戏曲的重要标志是好戏叠出”。特别强调“现代戏、新编的古代戏以及整理加工改编的传统戏都要重视”。总之,评价艺术的标准只有好坏之别,从无新旧之分。
固然,排新戏很重要,自己排演的新戏更能展现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采,更能招揽观众。不过新戏不是樱桃桑葚,货卖当时。新的汽车要磨合,任何新戏也都有个成熟过程,所谓十年才能磨一戏。足见新戏不等于好戏,新戏只是不成熟的戏,或者说是一出好戏的毛坯,只能说新戏成熟后可能是好戏。然而,不可想象的是某些创新者却一味地喜新厌旧,认为只要创新就不要继承传统了,甚至使“断裂论”泛滥一时。岂不知,你搞的戏曲已经800岁了,你排的京剧也快200年了,新戏再新,也离不开这个老的载体,离开了,也就不是戏曲,不是京剧了。
其实,惟“新”主义者并非真的喜新厌旧。同是艺术大师,他们讥笑京剧的谭鑫培太老,却崇尚比谭鑫培更老的约翰·施特劳斯;同为戏剧经典,他们对京剧《空城计》不屑一顾,却对同时代的舞剧《天鹅湖》推崇不已;他们称《贵妃醉酒》是陈腔老调,却又热衷更老的《蓝色多瑙河》;明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都是梅兰芳的崇拜者,他们却拿着“斯坦尼”的大棒去批判梅兰芳,或者把布氏捧上天,把梅先生踩在脚下,可见他们喜新厌旧是假,说穿了,只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是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作怪罢了。可以想象,鄙视京剧传统者,排演的戏怎么能有京剧的味道呢?


(大型新编史诗京剧《赤壁》“泛舟借箭”场景之一
编者刍议:
●在“创新”的时代,艺术领域自然也是“新风”荡漾。其实许多时候,很多文艺院团惟“新”也是无奈之举,创作费、场地费、排练费等都需要仰仗“新”作品评奖而来。其实像京剧、民族音乐等艺术门类的传统作品都是可以“常演常新”的,比如新的艺术处理、艺术表现以及艺术功底、艺术新人的评价等等,评奖缘何只认新作?
●对于观众来说,观赏艺术作品只是为了一次艺术审美体验,与作品的新旧是没有关系的,原汁原味的老歌是一种体验,老歌新唱、新歌初听也是一种体验。好比你可以一直喜欢茅台、五粮液,也可以喜欢新勾兑的饮料口味。对艺术的欣赏总是各有所好各取所需,可以有喜新厌旧的追求,当然也可以有百听不厌的自由。所以从评奖机制上只有惟“新”主义就不免偏颇,传统作品可以常演常新,观众也可以常看常新,有着丰富的“评头论足”的“资源”。
为京剧号脉(之六)——重技轻戏与重戏轻技
现在看京剧有两个极端,一个是15分钟的大奖赛,不要说表现人物,就是交代剧情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竞技大赛,嗓音大赛。结果是见技不见戏;一个是某些新编剧目,因为是话剧导演中心制,再加上剧本过分强调所谓的语言文学性,充其量不过是剧本式小说,演员的四功五法无用武之处,也就无技可谈。
其实,艺术前辈非常重视戏与技的结合,说"有技无戏不是戏,有戏无技难成艺"。例如当年叶盛章与黄玉华排演《秋江》时,为练习云步和蹉步等技巧竟磨坏了好几双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通过脚下娴熟的功夫来表现二人行船极其自然的状态。使观众看不到他们的脚在动,而是船在行;是要观众注意他们在船上那风趣的对话,而不是他们的脚步,也就是要把技巧表演完全溶解在意境之中,因此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为祖国的京剧艺术赢得了第一块金牌。现在不少演员却都是以观众的掌声论成败,拉长腔,洒狗血,跺台板。或者戏不够,出手凑,跟头从360度转体发展到720度,结果呢?观众的掌声越来越多,上座率越来越低。原因显然是技离开了戏。
更严重的是技巧的运用不是看水准,而是看数量。好象只要卖力气就好,台下翻三个跟头,台上却翻五个;演出的音调比练功的音调还高,让观众说“真不容易,鼓掌吧。”岂不知,观众要欣赏的是美,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又怎么能美呢?当年李少春和李万春与上海同行演《铁公鸡》,实际是南北武生大比武,别人的跟头越翻越奇,越翻越多,越翻越绝,最后二李以少胜多,打了三个普通的“飞脚”,不但又高又飘,而且同起同落同响,从而艺冠群雄,原因就是一个字:美。梅兰芳晚年杰作《穆桂英挂帅》,那“捧印”的亮相也是千古绝响,原因就是简练到了极点,只是一个转身举印的动作却产生巨大的艺术魔力,以他几十年的功力和造诣把技与艺结合到完美的境界,这才是真功夫,真艺术。遗憾的是重艺轻技的新编剧目,还是重技轻艺的大奖赛都走向了梅兰芳的反面。


(京剧《锁麟囊》“朱楼”一折寻球场景)
编者刍议:
●都知道技术或者技巧是手段,但是演员要突出它们的时候,当观众聚焦它们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就成为了目的。器乐中的快板“炫技”至少还有乐谱的“依据”,而京剧中的耍高腔、“洒狗血”,则常常是一种为了掌声而“没有底线”的“故意”。对于唱京剧的来说,应该自问一声:要掌声还是要人物;而对于器乐和声乐的演奏、演唱者来说,需要时刻告诫自己:要卖弄还是要倾诉。
●从文中的实例可以看出,使用繁复还是简练的技法,其实也都是手段,目的都是为内容、为情境、为情感、为人物服务。当然,高妙的技法无论繁简,都需要认真刻苦的打磨,才能化于心中、融于身形,服务于作品的演绎。曾经有国外的小提琴大师说过,好的演奏是看不见技巧的。这就像文中所说的京剧《秋江》,把苦练而成的云步、蹉步等技法,“埋葬”在了“平稳行船”的脚下,让观众只关注演员的情趣对话。
为京剧号脉(之七)——“专家评委”乱弹琴
众所周知,足球裁判不能不懂足球;研究计算机的不能不懂计算机原理;京剧的评委当然不能不懂四功五法。然而,在一次梅兰芳金奖大赛中却闹出这样一个笑话:在一次评委会上,有位艺术家建议:“评委打分后必须署名,因为有的演员荒腔走板不搭调,竟然有评委给满分,有的演员在耍枪花时掉了一次就扣掉两分,岂不知荒腔走板是水平问题,耍枪花失手是临场发挥问题。这样评分没有道理,谁错判谁负责。”不料这时有一位中国剧协的老领导,据说还是全国闻名的戏剧专家,却立即反驳说:“我不管那么多,只凭总体感觉。”这时全场艺术家愕然,心说:音调不准,板眼不分,总体感觉怎么能好呢?结果那次12位演员的评选结果,有些根本不合格的演员也都各有一票,真不知这一票的根据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是几位获得观众票数最多的演员,在评委那里却名落孙山。我想,这些评委评分的根据是什么,到底对京剧知道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某些评委讨论剧目时还有个三多三少:谈剧本的多,谈表演的少;谈总体感觉的多,谈具体表现的少;谈灯光布景的多,谈唱念做舞的少。他们的评奖理由不外三条:一是“突破了传统的框框”;二是“大胆创新”,越不像京剧越好;三是大投资,灯光布景大制作。至于这个戏能否面向观众,面向文化市场,排练成本能否收回来,他们便一概不管了。所以发展到今天,很多排演的新戏都在百万元以上,灯光布景都要四辆到六辆,甚至十几辆大集装箱车来装运,都要现代化的舞台设施。有些获奖剧目且不说演员表演平平,唱腔的基本功更是差得可怜。有个表现京剧“祖师爷”的戏,两度进京获奖,其实不过业余剧团的水平,真不知这巨资投入,这人民的血汗,如此白白浪费,为什么如此心安理得?且不说某些人靠这“评委”的招牌吃遍了全国的山珍海味,就是如此评奖方式,如此评委水平,对京剧的发展能有什么裨益呢?


(央视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场景之一)
编者刍议:
●艺术界有一句“常用语”说:“一百个导演可以导出一百个哈姆雷特。”由此可见,对作品诠释的主观色彩比重何其之大。竞技体育的比赛规则多有“量化指标”,但音乐、戏曲等艺术门类,除了音准、节奏等“浅层次”的“定量”指标,相当程度都是评委的主观考量,所以换个角度说,比赛考的其实是评委的专业功底和公德良心。如果问一声“评委谁来评”,或许就应该是观众来评。
●既然艺术的评价已经具有相当的主观成分,那么把传统剧和新编剧这种差异更大的、缺少可比性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更加无从比起。也许分类评判的尺度更为明晰,更具有操作性的做法,就是像“青歌赛”把“原生态”从“民歌组”独立出来那样。
为京剧号脉(之八)——轻视唱腔的音乐语言
为老的京剧演出录音配上图像,以保存艺术前辈演出的风貌,所谓“音配像工程”无疑是亡羊补牢的明智之举。然而,明明是自己演出自己唱,却要先期录音,再以自己之音配自己之像,也就是“对口型”,这不但是一种假冒伪劣的行为,更是对舞台艺术的糟蹋。尽管先期录音可以保证音质音量的水准,却无法通过录音的唱腔表达演员此时此刻的内心独白。有些演出,尤其是在电视台的演出之所以声音华美而不动人,原因也就在此。
京剧前辈筱翠花说,他一上台,用眼睛向观众一扫,就把观众的眼光紧紧地拢住,从此他的“神”就再不能离开观众了。当然,这个“神”不只是眼神,而是用你的唱腔旋律,用你的形体动作语言与观众进行心与心的勾通,全神贯注地交流。哪怕一个很小的动作,都要表达出自己的心声,都要有目的性,观众也才能受到感染。如果你的动作没有向观众说明你的心情,你的唱腔不是用你的心在唱,你用什么跟观众交流呢?有个黄梅戏的女演员说:“我在舞台上必须全神贯注,用自己的表演去拢住观众,稍微一放松,观众的注意力就跑了,整个剧场都散了,我要费很大的劲头才能把观众拉回戏里来。”所以她演出的两个半钟头里,剧场里非常安静,观众几乎都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足见凡是好演员,无论新的,老的,京剧的,还是地方戏的演员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演员与观众情感的交流与共鸣。因此当你在用心听录音对口型的时候,当你在假唱的时候,也就是演双簧的时候,你的表情一定是苍白的,唱得再好,与你的表情也不是一个整体,怎么可能拢住观众的注意力,又怎么能感人呢?
假唱不行,同样,用录音伴奏也不行。既然唱腔要唱情,感情就不能机械似地起伏跳跃。所以戏曲的伴奏节奏都是随着演员的感情相应变化的,唱腔要讲究个劲头,而这个劲头,就是要随着人物的情感变化而使唱腔或长或短,或起或伏,或疾或徐,京剧的唱腔就是这样有法度而无定谱。因此都是一样的曲谱,一样的唱词,由于演员临场处理不同,演唱的效果也就截然不同,有的感情充沛,有的呆板乏味,甚至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程砚秋的程腔为什么动听,就因为他的演唱是一种有章法的自由活动。如果用录音伴奏带或者由琴师看着乐谱“自顾自”的伴奏,程砚秋恐怕一个字也唱不出来的。可知死腔死唱是不会出神传情的,所以音配像式的演出或用录音伴奏的结果则如冷面人:无情无义。这也是目前观众认为进剧场不如看电视的原因之一。


(对优秀青年京剧演员进行舞台取像、专业录音、为音配像的录制称为“像音像”,以保证音和像都能尽善尽美。)
编者刍议:
●无论器乐、声乐还是戏曲工作者,在演绎作品的时候都应该时刻牢记:我们演奏的、演唱的是音乐,不是音符。
●所谓“京剧演唱是一种有章法的自由活动”,其实是一种赖于各种音乐情感的自由活动,所以也可以视为“有章法的情感活动”。在器乐、声乐表现当中也是这样,有些演奏家用民乐改编了像肖邦小夜曲之类的作品,如果机械地数着拍子演奏,那么浪漫钢琴诗人的韵味则荡然无存。
为京剧号脉(之九)——关于剧团的体制
眼下剧团还有个怪事:多大的“角儿”要唱戏,也得给四个头的龙套搭一份人情,演“出手戏”的武旦要哄着头杆和二杆。过去是龙套傍“角儿”,现在是“角儿”傍龙套。乐队为演员伴奏,应该是演员的随手,现在某些乐队演出看曲谱,演员只能跟着乐队跑;还有位院长说:“某某老生演出还要讲条件,还要自己挑琴师,选配角,告诉他,我们这儿唱老生的多得很,谁唱不行?”有的院团长动不动就要给某个主演“拿龙”,动不动就要让那个名角“晒他两年”,听来理直气壮,细想荒唐透顶。
记得当年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演出《群英会·借东风》却在广告上只写《全部借东风》,扮演周瑜的叶盛兰不满地对扮演曹操的袁世海说:“为什么不写上《群英会》,我们的戏那么重,难道还不如借风的一段唱吗?”袁对叶说:“这可不能生气,周瑜和曹操都换人,人家马先生照样卖票。马先生的孔明一换,就只能回戏了。别忘了,观众是听马连良来的。”一番话说得叶先生无话可讲。前几年,北京演出《画龙点睛》,广告号称“五个一级演员联袂演出”,结果张学津一人因病辍演,这出戏就没人看了。云南京剧院为什么享誉全国?是因为关肃霜;黄梅戏为什么脍炙人口?是因为严凤英;河南越调为什么五进北京?是因为申凤梅;北京为什么出现曲剧?是因为魏喜奎;京剧为什么家喻户晓,称为国剧?是因为梅兰芳。足见一个明星往往关系着一个剧种,一个剧团,一出戏的兴衰成败。因为观众就是围着明星转的。然而我们的剧团体制却不能围着明星转,以为人人可以唱戏,人人可以当主演,因此剧团对明星的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主演没有私房的琴师、鼓师和私房的行头,不能挑选实力相当的配角,就更不用说以主演为中心的编剧、作曲、导演和舞台美术设计了。唱什么戏,用什么身段都不能自己做主,明星的风采得不到充分的展示,明星也就失去了号召力,观众看不到自己向往的明星,怎么来买票?剧团的生存自然也就成了问题,京剧的振兴又从何谈起呢?
事实说明,剧团体制与演出市场格格不入,改革迫在眉睫,明星制势在必行。


(民国时期长安戏院程砚秋《聂隐娘》等剧目的京剧戏单)
编者刍议:
●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改变等诸多因素,使得京剧日渐式微,也许并非一个“演员中心制”就能“点石成金”。如今有多少明星演员有当年流派代表人物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思想,有梅兰芳能戏二百多出的艺术积累。而前辈们即使身处京剧兴盛的时代,依然有生存危机带来的发展动力。这一切的“底气”和担当,对于现代衣食无忧的“角儿”来说,恐怕是一时“难全”的。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挑班唱戏”的实验也多以失败告终。
●现代的京剧人如果能够静下心来认真传承、深刻解读、踏实积累,建立起扎实的基础已属不易。梅葆玖先生也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大师,充其量是个老师,能把父亲的东西守住就不错了。对于民乐人来说同样也有认真解读和研究琴谱筝曲、广东音乐、江南丝竹、福建南音等传统音乐的必要。
●京剧需要发展也的确是“硬道理”,早年的流派也是发展而来,也在不断“更新”。但这是一种“有根之木”的“新陈代谢”,是文化的渐进而不是蜕变。今天的京剧人、民乐人在寻求发展创新的时候,不妨设问一下:假如梅兰芳、程砚秋、刘天华活在当下,他们会怎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