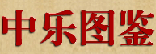编者的话:
百年前国乐先驱郑觐文创立的大同乐会,集演出、培训、资料曲谱整理、音乐创作、乐器制作等国乐活动于一体,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大型民族音乐团体。蔡元培、史量才、章士钊、欧阳予倩、梅兰芳等大批的文化艺术界精英或出资、或号召、或任教,可谓鼎力相助。虽然由于世事动荡,大同乐会存世仅数十年,但却以“全方位”探索积淀的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承上启下的地位。
在郑觐文“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的旗帜下,大同乐会群贤毕至,汇聚了众多的国乐大家,《春江花月夜》的改编者柳尧章就是其中一位。
虽然大同乐会同仁是为振兴国乐而“众志成城”,但毕竟开创的是一份筚路蓝缕的伟业,未知的前路、思想的交锋、条件的限制等,都是无可避免而需要全力应对的课题。从柳尧章的回忆录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国乐文化环境,以及那一代国乐同行者的所思所想、行事风格以及勤勉精进、执着事业等心路历程和细节。
专此推荐转自“春秋国乐”的《柳尧章回忆录》,并增加了相关图片资料与同好分享。
源文注:文中括弧内的字为柳尧章所加,而红字夹注系陈正生所校。(陈正生:原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音乐学家。)


柳尧章40岁(1944年摄)/源文所附
柳尧章(中尧),浙江鄞县(宁波)人。生于1905年(10月10日)。自幼爱好音乐,小时从父亲学习民乐琵琶、二胡、箫、阮等乐器。12岁(1916年)来上海求学(徐汇公学),同时从西人教授学习小提琴、钢琴(他又说向校长、意大利神甫Lawaza学钢琴,兼习小提琴和大提琴)。后自学管乐器和西洋乐理,经常到市政厅听上海工部局交响音乐会的排练(在市政厅楼上,后面可以免费进去听)。
1923年某日,《申报》登出郑觐文发表乐理论文(这几张连载的论文,我曾把它剪下来贴在簿子上,一直到1966年才毁了)。内容是关于律吕。他认为黄钟相当于西乐的C音,有的人认为林钟相当于C音)。我看了觉得他的见解和我相同,第二天我就去访问他。地址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004号。这是他弟弟郑立三家(应是堂弟),门口有块牌子“大同乐会筹备处”)。他有制好的改良箫、笛,我向他买了一支。与他讨论中西乐理,谈得很投机,从此我们天天在一起,成了很知己的朋友。
(1923年《申报》没有郑觐文的乐理论文,1923年只有一篇报道《大同乐会新组织--宗旨: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刊于11月17日。关于此内容的乐理论文,刊载于1924年2月13日,题为《大同乐会筹备修正中西乐》。但此文不连载,连载的出现于1929年,但内容与此无关。因此,此处是柳先生的误记。)


郑觐文非常注重乐器研究,大同乐会也设有乐器工场。20世纪30年代初曾主理制作乐器160余种,其包括了古代乐器、现存民间乐器、少数民族乐器和部分创意乐器。图为相关资料。
有一天,他介绍汪昱庭老师教我弹大套琵琶,一个同学是程午嘉先生。教了两个月,汪老师被叶寿臣(叶澄衷的孙子)请到他家中教他一个人。我和程午嘉二人于晚上去他家(在虹口唐山路)看汪老师。回来时已很晚。我们二人在外白渡桥下车。路上谈了很久,大家以为路途太远,而且在夜里不方便,以后就不去学了。后来我一个人每逢星期日上午去到汪老师家里(在王家码头,也是很远,因为在白天,比较好些)继续学习。在暑假内,到汪老师的大弟子王叔咸家里去讨教,听他弹奏。他弹得很好,真可谓青出于蓝。假期一过,他就去北京到协和医科大学读书。后来王叔咸先生在北京医学界很有声望。


1934年8月柳尧章的琵琶老师汪昱庭先生在上海参加浦江游览国乐活动留影


1934年8月俭德国乐社参加浦江游览活动由程午嘉演奏琵琶
1924年(6月8日),郑觐文先生送我票子,要我听他的女学生(基本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学的学生)演出雅乐音乐会。地址在上海市政厅,节目是雅乐合奏,有琴、瑟、钟、磬、埙、篪、排箫等乐器,唱的是诗经。我听了之后,认为雅乐太深奥,曲高和寡,而当时社会流行的是江南丝竹。我建议将琵琶曲谱《浔阳夜月》改编成四重奏,用琵琶、筝、二胡、箫四件乐器,加以支声复调。当时郑觐文先生很同意,并改名为《春江花月夜》。


柳尧章的琵琶曲谱《浔阳夜月》手稿。他据此改编了合奏《春江花月夜》
我把家里的阮带到上海,郑觐文照样仿制了一只,从此上海便有了阮。(按,阮在宁波本来有之,上海没有。上海只有双清,即今日之秦琴,式样不一样,性质相同)。现在的大阮、中阮就是从这个乐器改良的。后来我把它用在《国民大乐》,作为低声部乐器。


大同乐会所制阮遗存
1925年,我在上海美术转科学校担任“俗乐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刘质平。有一次通过父亲的朋友介绍到法商百代公司(现中国唱片厂)去上班,没有做事,坐了半天,看到外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很傲慢,经常骂工人,下午我就不去了,仍在美专上课。后来美专闹风潮,部分学生到打浦桥另开一个新华艺术大学,我就到那边去教(有些教师两边教)。
1927年,我制造大、小埙一套共六只,拍有照片。柳和埙就在这一年出生,因此取名为和埙(和字是排行)。
1931年开始编译琵琶谱和七弦琴谱,按照西乐理论采用五线谱译成《霓裳羽衣曲》,改编成重奏。
1932年,正值“八.一三”(应是一.二八)事变,国难当头,无意弹奏音乐,每天在炮声中把编译的曲谱全部完成。
1935年,教柳和埙小提琴,时年8岁。到12岁时参加全沪儿童音乐比赛,得小提琴第一名。(该次比赛为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举办,时间为1940年3月2日,应是十三岁。当时柳和埙所用之名为柳仲篪。)


柳尧章之子、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柳和埙(右)与指挥家陈燮阳(中)和爱好指挥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合影。
大同乐会曾经有一次中西音乐家会演,是世界着名小提琴家秦巴里斯特(Zimbalist)小提琴独奏,我演奏的是琵琶《十面埋伏》、《塞上曲》,郑觐文演奏古琴《秋鸿》和大瑟《寿阳宫》(即琴曲《梅花三弄》)这次招待演出的是李祖贤(已故)(李祖贤是胡适读北京大学和留美时的同学,与音乐界接触比较频繁)介绍。在场有着名诗人徐志摩(已故)和唐瑛女士等。地点在《字林西报》记者(沙哥士)家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此次会奏为1927年11月6日,参加者有胡适,而无徐志摩。)
有一次在《申报馆》经理史量才家里,史量才邀请汪昱庭与朱英会晤。二人都是李芳园传授的。汪老师奏《十名埋伏》,朱英奏《浔阳夜月》,我奏《塞上曲》。这二位大师能叙在一起是很难得的。
有一次在联欢会上,我与儿子、侄女演奏西乐三重奏。后听到朱英奏《十面埋伏》,他弹到“百万军声”一段极精彩,全场肃静。我听了很受感动,把他的奏法采用,编入我所编的琵琶谱里。


朱英(右)给弟子杨大钧上课
有一次应黎锦辉邀请参加“梅花会”。地点在威海路中社,演奏《春江花月夜》和《霓裳羽衣曲》。黎锦辉先生答谢来宾,把他创作的儿童歌剧《葡萄仙子》由他的女儿黎明晖女士主演。
有一次在史量才家,演奏《春江花月夜》和《霓裳羽衣曲》。演奏者是我和他的亲属们。在场的有梅兰芳、程砚秋、何东爵士(香港人,属爱国华侨,受英国女皇册封)等。梅兰芳曾为我编的京剧唱片谱题字。
我有个时期常到施颂伯家里听他弹《龙船》、《十面埋伏》和一些小曲,如《飞花点翠》、《汉宫秋月》等。他是崇明人,弹的是海门沈肇州派。(施是沈肇州的早年弟子)。


1916年沈肇州原版《瀛洲古调》(崇明派)。封面为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沈恩孚题字。(杨刚提供)


1916年沈肇州原版工尺谱的《瀛洲古调》之《飞花点翠》(杨刚提供)
大同乐会到外面去参加演出,节目是独奏、重奏,多数是郑觐文和我担任。后来有个年轻的会员王寂红,他弹得一手好琵琶,指法同传统的指法一样,但不会弹大套,(实际上学的是大套琵琶,只是不爱弹),而是弹自己编的曲子《满城风雨》,编得挺好。可惜只有此一曲,有时外面常请他去演出。(王寂红原是欧阳予倩的学生。欧阳予倩来沪后,将他带来上海,离沪后托付给郑觐文。王寂红原名王安详,来沪后所改之名。先改名王泣红,郑觐文认为此名不吉利,劝他改名王集鸿,不听。1932年病死于黄山。)
我对郑觐文说,外面的音乐虽然已经改革,但是规模太小,没有大型合奏。我想把全上海的音乐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乐联合会,共同搞好民族音乐。郑觐文很赞同,就发信给各团体,请他们出席参加。那天是全到的。著名的团体有钧天集、中华音乐会、霄雿乐团、国乐研究社等。(此次会议没有钧天集,时间是1929年5月。参加的十个团体是:大同乐会、汪氏琵琶研究会、霄雿乐团、韩江丝竹会、琴侣斋、精武体育会、中华音乐会、辛酉学社、华乐团、俭德储蓄会)当时由郑觐文致开会词,接着我发表了意见,要把演奏的方法统一,按照编好的乐谱,要大家看谱演奏。来参加者也有很多人发言赞同。最后我对他们说,下次开会再发通知,结果第二次开会到的人就很少。可知当时搞民乐的人都比较守旧的,大概他们以为这样做要变成不中不洋了。


1936年霄雿国乐团庆祝成立十周年活动留影
后来我与郑觐文商量,办个国民大乐队,登报招收学员(1929年9月)。结果来了很多演奏者,大部分是邮务工会民乐队的,卫仲乐、许光毅、许如辉也在此时加入。我编好一首套曲《国民大乐》,按照我上次计划来排练,看谱演奏(暂时用简谱),约有三、四十人。到南京演出的一次,我在火车里把台上每个人的位置与出场的先后次序排好。这次演出很成功。此后我想进一步搞好这项工作,要求每个队员都学会五线谱。这一点就有人不赞成,连本来相信我的郑觐文也不赞成了。意见分歧就无法再搞下去了。(根据柳先生的提示,此次南京之行应当是1931年夏天之前,但查不到实证。1926年8月,大同乐会应江浙五省司令孙传芳宴请赴宁,参加投壶典礼。据卫仲乐先生会回忆,柳尧章与郑觐文的意见分歧,乃是对“七线谱”的意见不统一。若此事属实,乃是1931年夏天的事。)


1933年4月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为大同乐会演奏《东方大乐(国民大乐)》拍摄纪录片的留影。
后来教西乐(即1932年夏于“梅兰坊”--现今的四明村--93号办的“中西音乐研究室”),办业余交响乐队,乐谱都是我一个人从总谱抄成分谱。开始时大家很积极,但是很浅,到了有点成绩,反而不积极了。最兴旺时候有过30人。曾经参加者有张子玉、朱世杰、王伯洪、朱启东、司徒海城、司徒华城、刘君瑞、韦贤彰、陈怡一、唐国枢、张元吉、黄源爵、陈新庭和我的学生。排练过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和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等。到那时,交响乐都成了临时交响乐了。我改变方针练弦乐队,后来又是一样。最后又练弦乐四重奏……
1964年我60岁,教外孙顾维舫小提琴,他三足岁。先拉空弦,练半年后才正式开始。教了8年,很有成绩,到北京跟林跃基学三星期。因老师编中国教材没有空,跟他的学生夏三多学。夏老师生病,再改从隋克强老师学。1981年下学期投考上海音乐学院大学部,被录取。1982年上半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国内选拔赛,上海音乐学院17岁的薛传和19岁的顾维舫入选,准备七月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卡尔费莱希国际小提琴比赛。
1925年我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时,有一次我在学生宿舍遇到一位华侨同学,听他弹夏威夷吉他。有一首歌很好听。他不懂谱,也不知道这首歌的名称。事隔一年之后,我想再去听他弹吉他,到学校去找他,别的同学对我说,他已转到真如暨南大学。于是我就乘火车至真如暨南大学,果然找到他。他倒还认识我,他又弹给我听几遍。我把这首歌的旋律记住,弹奏的方法看清楚,回家后练了一个时期就会弹了(柳老是上海吉他学会的顾问)。我想到年轻时没有谱,凭记忆力能够学会,到现在(78岁)记忆力衰退,连拉京戏也要看谱,不看谱就一只也不会拉,使我不胜今昔之感。


柳尧章80岁(1984年摄)
关于《春江花月夜》的改编与《霓裳羽衣曲》的整理
我从汪昱庭老师处学会的《浔阳夜月》,原谱是工尺谱,谱上的节奏只用“、”来表示。如果要把它译成简谱或五线谱,第一个难题就是首先要把几拍子肯定下来,然后再看音乐是否需要增减或改动。这步工作就是整理。到改编时,因为乐器增多了,这时乐曲分段必须有所不同,再加上支声复调,和原曲就不能完全一样。因此,郑觐文先生想把它改名为《春江花月夜》,我也同意。有一次有一位张肖虎来到大同乐会(此事应在1932年之前),他是研究西洋理论作曲的。我弹《春江花月夜》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对我说:“这首曲子可以改编成交响乐”。听说张肖虎同志现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1991年柳尧章亲笔简写的“《<春江花月夜>产生的过程》”手稿。1925年柳尧章将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后,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为“新丝竹曲”,评价为“没一点尘俗气”,不听此曲引以为憾。在另一篇柳尧章口述、陈正生整理的《我是怎样改编<春江花月夜>的》文章中,还介绍了此曲名称的变迁:“乐曲改编完以后,觉得再用《浔阳夜月》的曲名已不够妥当,便根据白居易《琵琶行》‘春江花朝秋月夜’的诗句,易名为《秋江月》。《秋江月》改编好以后,总觉得这一名字不能体现出乐曲的意境。1926年春,郑觐文先生仍然根据白居易的诗句再次易名为《春江花月夜》,并在每段前面冠以小标题。演奏过程中也曾增用过忽雷、卧箜篌和钟、磬。”
《霓裳羽衣曲》在华秋苹琵琶谱名《月儿高》。当时我没有听见人弹过。汪老师也不弹的,大概是因为乐曲长而沉闷吧。我是根据华秋苹弹奏,觉得此曲优美。华乐谱的“西板”,许多曲调照原谱弹是不好听的,非经自己加工不可。我按华氏谱上的《月儿高》一个字也不改动,象弹钢琴一样照谱弹,只要自己能懂得它的曲趣,有些地方庄严,有些地方活跃如舞蹈,弹出来不同凡响,有些象交响乐的风格。我弹会后,有一次弹给郑觐文先生听,他听了叹为观止,竟然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之感慨。(此事应是1927年5月之前)我又把《辞海》里见到的说法讲给他听:“唐朝叶法善法师引明皇游月宫,闻仙乐,归儿记其半。后婆罗门国进《霓裳羽衣舞》,音节与之吻合。”他听了也有同样想法,因此我把此谱加以整理后又改变成四重奏。


1927年初,柳尧章将《华氏谱》(华秋萍、华子同合编,1818年出版,最早印行的琵琶乐谱)中的《月儿高》挖掘、整理成琵琶独奏曲及合奏曲《霓裳羽衣曲》。
写在后面
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搞过改革民族音乐,有较长时间搞过西乐。可是都没有成就,虚度了七十八年。以上回忆是凭我自己想象(记忆)写出来的。因时隔太久,有些年份与实际未免有些出入,特此声明。
注:文中括弧内的字为柳尧章所加,而红字夹注系陈正生所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