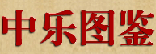恳请作曲家:千万别把江南丝竹写“死”了——采访资深江南丝竹玩家陆勤康(一)
受访者:陆勤康(上海资深江南丝竹玩家) 访问者:陈书明(《中乐图鉴》特约编辑) 摄 影:沈正国 访问日期:2017年7月18日


访者旁白: 江南丝竹是民间丝竹音乐的一种,形成于明清时期,流行于江浙一带。民国时期江南丝竹在上海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 “清平集”、“均天集”、“逸响社”、“俭德国乐团”、“中华音乐会”等众多江南丝竹社团。江南丝竹经常演奏的经典曲目有“中花六板”、“欢乐歌”、“行街”等八首,被誉为“江南丝竹八大名曲”。 记得十几年前偶然见过几次玩江南丝竹的,有的是自娱自乐的雅集场合,有的是表演性的演奏。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操弄笛箫、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玩家怡然自得、自我陶醉的神情。尤其是一曲终了轮换乐器的玩法,真是尽情尽兴地彰显了“艺多不压身”古训,令观者叹服。 与资深江南丝竹玩家陆勤康老师相识大概也有三十多年,知道他的江南丝竹乐队曾经长期“坐阵”豫园湖心亭茶楼。一直以为那就是一群乐友经常“过把瘾”的文化生活而已。但这次在长桥社区学校的采访和观摩,才使我真切感受到数十年沉醉于江南丝竹的陆勤康老师,不仅是一个资深玩家,更是一个资深江南丝竹的研究者。尤其是当下的江南丝竹,能够玩出高境界的人已是寥寥无几,而一些音乐专家还在不断对其进行“西化”改造,使江南丝竹面临着从“绝活”走向“绝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陆勤康老师依然坚持不懈地为纯正江南丝竹的生存和发展奔走呼吁,极尽奉献,堪称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江南丝竹痴心的守望者。 这次的采访录音整理出了两万多字,现辑录分享在此。


民乐合奏是写出来的,江南丝竹是玩出来的。 访:陆老师,刚才看你们白相(玩)江南丝竹,老有味道啦。每个人 手里出来的旋律,听起来是“时分时合”自由自在,但又是同一走向,而且是自得其乐老惬意的。这和民乐合奏那种刻意雕琢的感觉完全两样,请你给我聊聊这两种形式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感受。 陆:其实你刚才说的感受当中就已经包含了基本的答案。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感受,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艺术形式的音乐作品,在形成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访:这听起来有点玄乎。在一般人看来,本质上不都是一群人拿着相同的乐器在那里演奏嘛。 陆:这你是偷换概念。一群人和一批乐器那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我们要聊的是音乐的本质。 访:你说得对。那么两种音乐的本质差别又体现在哪里呢? 陆:我刚才说了。主要是形成方式和表现方式上的差别。你知道民乐合奏都是由作曲家制作完成的“成衣”,从旋律、速度、节奏到和声、配器甚至表情记号等等,都为演奏员立下了“规矩”。这样的乐谱把演奏员就基本绑死了,你最多能扭动几下。也许遇上一个有想法的指挥,可以让乐谱稍稍“松动”一下,但绝不可能挣脱。要不然人家作曲家也不干呐,因为你破坏了我的原创啊。 访:对,指挥也好、演奏员也好,谁也不敢侵权呀。那么江南丝竹又是怎么弄出来的呢?作为民间音乐应该是找不到作曲家的吧。 陆:你听说过哪个江南丝竹传统乐曲明确是谁作曲的嘛?应该没有吧。江南丝竹大多是基于民间小调或改编古曲逐渐形成的,也许很多音乐元素就来自于穿弄堂的剃头师傅、磨刀人随便哼哼的小曲。他们不可能有作曲配器的本事,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著作权。打个比方,这些民间小调好比是给江南丝竹的作品形成提供了一块布料。表演者可以在这块布料上随意裁剪、涂抹、修饰。 访:那具体到江南丝竹的音乐上,你们是怎么使用这块“布料”呢? 陆:首先,传统江南丝竹的每一个作品都有一条基本的、简单的旋律线,我们称为“母调”或“母音”,这条旋律线通过速度、节奏等音乐元素,确定了作品在情绪、情感上的基本走向,然后我们通过支声复调等技法,以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嵌档让路等表现方式,非常丰富而富有变化地包裹着“母调”这条旋律线一路向前走。从某种角度来说,江南丝竹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分秒秒在创作的过程,而且是每遍不一样的、不断翻新的创作。而所有这些手法的运用,都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即兴发挥式的。 访:这个感觉倒是挺符合逻辑的。我的理解是,既然江南丝竹这些“母调”,可以来自于做弄堂生意的人自由自在随便哼哼的民间小调,那么演奏的时候当然也应该是自由自在的。有其“母”必有其子嘛。 陆:哎,你这个说法倒像是为江南丝竹即兴的、自由自在的演奏找到
了“理论依据”。 访:那么按照这么“自由主义”说法,这么即兴的做法,你们在演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比如说《行街》,是不是每次演奏出来的音乐、味道都是不太一样的? 陆:当然不一样。像《行街》呀,顾名思义就是到处走街串巷,边走边奏,那一路上的风景当然是各种各样的。再加上红白喜事心情不一样,我们的变走哪能会是一个味道呢?你说是不是? 访:那每遍不一样,演奏的人是不是会觉得很麻烦? 陆:怎么可能呢。不一样才好白相(玩)。一方面即兴演奏的东西想要每遍都一样也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方面,要是每一次雅集、每一遍演奏都是一样的,那不是和死板板的民乐合奏一样啦?那还有啥白相(玩)头啦。 访:哦,对,是我问糊涂了。那按照这样艺术形态,你觉得如何来定义江南丝竹比较恰当呢。 陆:关于江南丝竹的定义,我觉得可以从相关的名称进行比较。我的理解是:丝竹,或者说丝竹音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中国传统的弦乐器和竹管乐器为主的传统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各地都有,品种很多,比如广东音乐、潮汕音乐、陕西民间音乐等,当然也包括江南丝竹。
访:那中国的民族乐器以弦乐器和竹管乐器居多,按照这种说法,差不多玩民族乐器的都可以归入丝竹乐了。
陆:错!请注意我说的是丝竹,不是丝竹乐。你可以说差不多玩民族乐器的都可以归入丝竹或者丝竹音乐,但不应该说归入丝竹乐。
访:那为什么呢?
陆:因为从现实情况来说,丝竹乐也是丝竹的一个品种。比如一般的民乐作品中,只要引进了江南一带风格的音乐元素,或者使用了传统江南丝竹的音乐元素,应该就可以称为丝竹乐。而江南丝竹自民国开始逐渐以上海为中心进行传承,应该是一种地域性的民间音乐品种。
访:哦,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丝竹,不等于江南丝竹,也不等于丝竹乐,但是涵盖了江南丝竹和丝竹乐,两者都是丝竹范畴里的两个音乐品种。
陆: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江南丝竹和丝竹乐虽然都是属于丝竹范畴,表演形式也差不多,但他们的形成方式和表现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访:这种不同,应该就是刚才说的作曲家裁剪的“成衣”,与民间的“布料”裁衣的差别吧。
陆:是的。
访: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丝竹乐理解成为一种具有江南音乐风格的民乐合奏。
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此地我要特别声明:所谓民乐合奏与江南丝竹本质的不同,不是指艺术上的高下之分,而是各自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的不同所决定的。就像有的人喜欢逛街,在各种各样的“成衣”里面挑自己喜欢的一款,而有的人就是喜欢买“布料”,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衣服。
访:哎,这倒也是。不过现在买“布料”的人还真不多,就像你们玩江南丝竹的也算是比较“小众”了。
陆:这也是事实,但是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不管“小众”还是“大众”,这个与艺术的高下没有关系。你不能说江南丝竹玩的人少就是“淘汰”产品,那也许是因为“曲高和寡”呢?
访:这个说法我同意。关于艺术高下的问题,只能说由于艺术水平的高低,“成衣”里面会有不同的“档次”,那么“布料”裁衣也会有不同的品质。而“成衣”和“布料”应该属于两个类别,其实是没法比较的。
陆:这样说就比较客观了。从作品的打造直到作品的呈现,民乐合奏本身会有艺术的高下,江南丝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方面。而两者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又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玩法”。民乐合奏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尽最大努力,由作曲家、演奏员、指挥以及调音师等,合力打造和呈现一部经过精打细磨的完美作品。所以有些地方还真是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就会变味或者变质。而喜欢民乐作品的人就是要享受这种完美。
访:对,这就必须把一切都定死,越细致越好。
陆:所以你看,用民乐合奏写法“生产”的丝竹乐作品,一开始经常会有一两分钟的引子,当中要弄点抒情啊、高潮啊什么的,最后或许还有一个尾声。这些结构性、细节性的东西,都体现了作曲家原创性的价值。然后在这个模本的基础上,再由演奏员、指挥等乐队成员来立体化完成一件音乐“成品”。也就是说民乐合奏的演奏员,已经是这件“成品”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自说自话地演奏来破坏“成品”了。
访:这是自然的,怎么可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陆:但江南丝竹不是这样的,不管是演奏者还是听众,都不是那种在美术馆办画展或者看画展的心态,而是玩。演奏者是“看我怎么玩”,听众就是“看你怎么玩”。江南丝竹不太讲究什么引子啊、尾声啊,而是音乐声一起,就直奔主题,然后开始尽兴白相(玩),可强可弱、可快可慢,可长可短,甚至转几个调再玩。江南丝竹虽然没有大型民乐合奏作品的那种主题啊、情感啊,那种大起大落的表现力,但同样是有着丰富的情绪在起起伏伏。
访:对,可以有优雅的激动,也可以有内敛的兴奋。
陆:最重要的是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跟着一条“母调”可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即兴发挥。
访:哎?我忽然就想到了,假如把《彩云追月》啊、《茉莉花》之类与江南丝竹风格相近的民乐作品,把它们的主旋律抽出来作为“母调”,用江南丝竹的方法可以玩吗?
陆:可以啊。你就是《二泉映月》这样的曲子,你想演奏五分钟也可以,想演奏20分钟也可以,看情况、看心情都可以操作。
访:这个放在民乐合奏上是不可想象的。
陆:所以简单地说就是,民乐合奏,包括丝竹乐,都是作曲家写出来的,或者说是写死的、不可以“乱弹琴”的一个成为了定势的“成品”模本,那是为了给人听的,甚至是给人看的。而江南丝竹是给自己玩的,是民间自由玩耍的,并且是可以玩得很“活”的、很自由的一种民间音乐。所以对江南丝竹来说,也许可以归纳出一个“母调”的乐谱,但由于每一次演奏,都会有自由的变化,自由的“玩法”,有不一样的版本,所以总谱是没办法弄的。
访: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总谱永远在路上”。
陆:对对对,很贴切的一个说法。
访:所以在我的理解看来,这种“给人听、给人看”和“自己玩”的区别,其实就是刚才说的民乐合奏与江南丝竹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而这种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决定了它们的形成方式和表现方式的不同。所以民乐合奏的“给人听、给人看”和江南丝竹的“自己玩”,应该就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而从这个本质的角度来说,两者其实也就没什么可比性。
陆: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民乐合奏追求的是尽善尽美的呈现,所以要有精雕细琢后的定位,要做“死”;而江南丝竹追求的是尽情尽兴地玩乐,所以可以随着“母调”自由自在地自娱和娱人。
江南丝竹是一种玩“绝活”的民间音乐生态 访:我在刚才听你们演奏的时候,的确是感受到了这种自由。而且听上去每件乐器都是“自我陶醉”地、若即若离地跟着“母调”走,却一点也没有你争我抢、杂乱无章的感觉,反倒好像是互有默契,相得益彰。这种玩法真是挺绝的,我想想要玩好应该挺难的吧。 陆:你的感觉是对的。我们都搞过民乐合奏,你知道那个东西通过看着谱子训练、排练,一段时间下来也就基本完成了。有些能力强的专业乐队,拿起谱子几遍下来就可以八九不离十。但是江南丝竹不行,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说,它的乐曲演奏难度、乐器演奏技巧什么的都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甚至可以说谈不上什么难度,但真的能这么自由自在地玩起来,玩出它特有的味道,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了。 访:这一点我相信。不依靠炫技,不依靠复杂的音效交响、也不依靠那种多乐章的结构、复杂的织体或者大开大合的情感表现什么的,就是一种简单的音乐风格,要玩得有滋有味,其实是体现出了江南丝竹更深厚的功底和更高的文化价值。所以看了你们的演奏,我就觉得玩江南丝竹的难度不在于演奏技巧的高深,而在于音乐感觉的积累。 陆:你这是一针见血的内行话。我经常讲,如果是一天泡一杯茶来玩江南丝竹,没有1000杯茶,也就是三年的功夫,你是摸不着江南丝竹边的。然后你想要玩到一定的境界,没有十年的功夫是体验不到那种美滋美味的。当然,如果你只是瞎玩玩或者简单的过过瘾,就另当别论了,那是玩不出味道的。江南丝竹玩出来的音乐味道怎么样,差异是很大的,这完全取决于演奏员积累的玩法有多少,当然还有玩法的组合、与其他乐器配合的悟性,更深一层的差异还在于对江南丝竹理解的境界和文化底蕴如何。 访:我们先不说高境界的东西,就玩法的积累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有点像钢琴的即兴伴奏。好的演奏员一定是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伴奏织体和方式,可以伴奏得非常自由灵活、非常多姿多彩。积累少的演奏员或许只能混混正三和弦、弹弹节奏了。 陆:但是你要注意,钢琴伴奏只是演奏员一个人的事情,而江南丝竹是一个器乐组合,这里面还有一个互相影响和互相配合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在看我弹阮的时候,我就要听笛子、二胡、扬琴、琵琶那些乐器它们怎么走向。这么多年配合下来,这几件乐器,这几个演奏员,他们的走向基本上我都知道,我就可以绕开他们走。他们在放长音时,我就可以用过渡音什么的,对吧。要是我敲扬琴,我就可能是另一种玩法。虽然原则上是大家跟着我走,但我也会做好所有人的替补。就好比我的扬琴像一座桥,二胡、琵琶、笛子等各种乐器可以到我的桥上来玩一下,也可以通过这座桥,让它们之间过来过去互相玩玩。 访:这个玩法大家在一起真是要很高的默契度了 陆:这是肯定的。 访:我刚才还看到你们演奏的时候,会经常换几个人上去演奏,而留在上面的人也会换几件其他的乐器演奏。这样的重组,配合出来的味道应该也是有变化的吧。 陆:当然。每个人的演奏习惯是不同的嘛。假如换个人来演奏同一首曲子,有时候就像“换人如换曲”一样,让人觉得“口味”全变。即使是同一个人换了一件乐器,由于演奏技法的运用、音色控制的差异和乐曲变奏方式的不同选择等等原因,味道也会大不一样。就像有一次开研讨会,许多国家级音乐院校、院团都有人来参加。我在展示我们《行街》这个曲子的时候,特意安排了一个我们平时玩江南丝竹时常有的情节,就是演奏半当中拉二胡的人突然去接电话了,其他人马上顶了上去。而那个接电话的回来一看二胡有人顶了,他就去弹阮了。这两次换手,整个音乐的过渡都很自然,但是味道都有变化。 访:这可真是玩得出神入化了。我们先抛开这种精神生活、精神享受不说,单就玩的乐器来说,人家京剧乐队一个人能玩多种乐器,也就是“六场通透”了,你们可以“十八般武艺”都能玩啊。这种玩法得是什么样得一种劲道啊。 陆:这种劲道就是来自于对江南丝竹一种说不清楚的热爱。就像我玩过戏曲,也玩过民乐合奏,玩来玩去,还是觉得江南丝竹最有味道。江南丝竹的这种玩法,它是一种你来我往的“手谈交流”。像倾听也像是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比是在心手合一的“嘎讪胡(沪语指聊天)”当中,达到了心灵交融。那种轻歌慢语、和谐雅致、缠绵温情、欢乐祥和、自由洒脱的音乐情绪,真的是体现出了典型的、江南的人文风情,体现了上海人的包容共生和从容气度。那种对音乐理解和演绎能力,似乎已经是融化在血液当中。 访:看上去江南丝竹就像“五香豆”一样,可以算是上海的特产了。 陆:所以我一直觉得,江南丝竹就是一种区域音乐,一种地域文化。对我们这些玩江南丝竹的人来说,能够经常聚在一起弄上几曲,互相交流各有所得,然后吃吃饭聊聊天切磋一番,就是人生一大文化享受。 访:哦,你们也有切磋的时候? 陆:有啊。像老早我们在城隍庙湖心亭做(定点表演)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五点钟,结束以后,把老酒、菜买回来,一边吃一边聊。然后晚上开始活动,有单人的“过堂”,有两三人的组合,也有全体合乐,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磨合、调整,来更新我们的“玩法”。我有时也根据每一个队员的特点,写一些比较简单的小型合奏,来进行音量、音色以及变奏、配合等方面的乐曲处理训练。这些也都是为了更好地玩江南丝竹服务的。 访:怪不得当年在湖心亭听你们的江南丝竹会感觉这么默契。当时我就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享受这种过程。我们还经常到外地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带上乐器去玩玩,那才叫在大自然当中享受天籁之声呐。对了,明天我们大概有三四十人又要一起去浙江了。你看这一切全是得益于江南丝竹的成全。所以对我们来说,江南丝竹就是我们的一种音乐生活形态。 访: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就好像江南丝竹和你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陆:就是说呀。所以江南丝竹在我们眼中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食粮,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时间上和精神上都是付出的,但我们就是很享受这种精神生活。 访:我突然想到,就是你说的这种精神生活,你们在物质上、时间上还都是付出的,这可能和30年代上海江南丝竹兴盛时期的情况有点相像。那个时期玩江南丝竹的应该也是那些有钱的和有闲的人吧。 陆: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应该是这样。那时的江南丝竹社团有不少就是银行、邮政、商界等有钱阶层办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底蕴,所以玩出来的东西比较有味道,有境界,这也反映出了他们比较悠闲、优雅的生活状态,一种音乐生活的雅韵。这个与田间地头农闲的时候过把瘾玩出来的江南丝竹,那种田园乡风的野趣,是不一样的江南城乡景致。 访:反正不管城里人有钱还是乡下人有闲,我看你们这里的江南丝竹玩家,都还是具备了一定条件的。 陆:当然都还是能够出来玩玩的。但那时的有钱、有闲,和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毕竟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了。关键是抛开有钱有闲的问题,以江南丝竹生存的社会环境比较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玩江南丝竹,更多的是出于对这种音乐生活的喜欢和热爱。 访:对,三十年代江南丝竹玩的人多,或许还会有附庸风雅的玩家,现在纯粹就是自己热爱的一种音乐生活了。 陆:就是啊,江南丝竹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种过日子的盼头,就像一个整天牵挂于心的孩子。你要是一支江南丝竹乐队里如果有一些不太会玩的演奏员加入,那种音乐效果一听就知道打折了,这种时候我们会觉得浑身难受。这种难受不仅仅是觉得玩音乐的感觉没有了,更觉得好像是身心受到了伤害。像过去我们一起在豫园湖心亭茶楼玩江南丝竹的几个老先生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直接上去把玩不好的人手中的乐器夺下来。虽然这也是有点过分,但这个湖心亭的江南丝竹毕竟是个人文景观,你瞎弄八弄总不像样。 访: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你上去玩,真的会破坏人家美好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就等于是去欺负人家的孩子。人家没有好日子过,当然就不让你干了,这也算是“正当防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