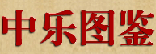作者:上海艺术研究所 陈正生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提倡争鸣,郑觐文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也越来越获得更多人的认知。可是要获得对郑觐文较为全面的清晰认识,却也并不太容易。这不仅是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急功近利倾向,也因为资料难求。我对郑觐文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是在《申报》上查阅到大同乐会的大量资料,并从郑觐文的弟子——我的老师金祖礼、卫仲乐,以及柳尧章、许光毅诸先生那里听到郑觐文先生许多轶事之后。记得有位学生写毕业论文向我求助,我将《申报》上搜得的大同乐会资料全给了他,毕业论文完成后告诉我,仅按图索骥式的查对我给他的《申报》资料,就耗时一月!当我有机会看到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以后,对郑觐文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除了个人著述以外,国家立项的音乐工具书没见收录郑觐文的词条,例如1985年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连已故的陆修棠都收了,可郑觐文就没收;1992年《中国音乐词典(续集)》仍然没有补收。何故?看来这同《辞海》“郑觐文”词条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
郑觐文一生有多部著作:
1918年11月,得周庆云资助,郑觐文根据《诗经》译谱的《雅乐新编(初集)》
由丙辰杂志社出版。丙辰杂志社的主管,乃是与郑觐文同住一起的堂弟、对易学和雅
乐深有研究的郑立三。
1924年10月,《箫笛新谱》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署名为“大同乐会编辑主任郑
觐文撰”。
1928年5月,《中国音乐史》脱稿,由其子郑玉荪校对,并征求大同乐会的基本
会员和上海音乐专家的意见。1929年6月,得周庆云资助、题签出版。
此外,郑觐文至迟于1922年便开始撰写《琴学源流》和《中西乐器全图考》,而《中西乐器全图考》一书,于1929年夏便已完稿,后因动乱,此稿竟不知所终。
《辞海》郑觐文词条对郑觐文的介绍是,“能弹琴和琵琶”;“创立大同乐会,旨在提倡‘国乐’”,其功绩也仅仅是“仿制各种古乐器”并“大事宣传”,目的也仅仅是“崇‘雅’黜‘俗’。”所著《中国音乐史》是“持论迂远,杂有臆断”,而“所编《箫笛新谱》一书”,也仅仅是“录存不少民间曲调”而已。
先看看郑觐文弹奏琵琶和古琴的情况。郑觐文1883年即已通普通丝竹而开始学大套琵琶,1888年开始向唐敬珣学琴。参加过1919年秋的苏州“怡园琴会”和1920年秋上海“晨风庐琴会”,并经常参加晨风庐琴社活动而成其中坚,领导琴侣斋的琴学活动,其琴艺深获周庆云、史量才的称道。所弹大曲就有《秋鸿》、《广陵散》、《水仙操》等,就更别说另有琴趣的《梅花三弄》和《平沙落雁》了。这水平难道也仅仅算“能弹”?显然有失公允!
需要说明的是,为送往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参展,4月9日晚,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了有声彩色国乐演奏纪录片。此次拍摄由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张群主持。纪录片一共拍摄了四首曲子,第一个就是郑觐文古琴独奏《水仙操》(当时易名《海岛孤踪》)。可惜当时郑觐文正患手疾,所以沈知白先生批评四个节目,“卫仲乐先生琵琶独奏《淮阴平楚》”,“真可说是炉火纯青了”。“郑先生的古琴最为逊色”,“那时臂患痛风,腕底无力,他虽然聚精会神,用尽气力,结果还是使听众大失所望①”。
关于《中国音乐史》,我想一般的读者别说见不着,就是拿到手恐怕读起来也很费力。笔者觅到至今三年多,也仅仅草草浏览而已,说实话,其实没有能力、也没有心力研读通透。所谓“持论迂远”倒未必,而“杂有臆断”实乃在所难免,何况“臆断”的程度远逊于今日——笔者常见《音乐研究》上就常刊有令人哂笑的文章便是证明。
至于“仿制各种古乐器”并“大事宣传”,为的是“崇‘雅’黜‘俗’,”这评价才是词条撰写者的主观臆断。而沈知白先生就认为,“像大同乐会改造乐器那样的工作,确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②近来见到郑觐文所著《箫笛新谱》,更证实郑觐文“一味复古”和“崇‘雅’黜‘俗’”的评价,确实有失偏颇。
就书名而言,《箫笛新谱》一书的意旨当然是谱。可该书却分上下两卷:上卷为“理法”,下卷为“曲谱”——而且是为“便于普及”的简谱。下卷共收有曲谱44首。按郑觐文的分类,其中共收“笛家专曲”34首,而“普通乐曲”仅有10首。所谓的“笛家专曲”,并非箫笛独奏曲,乃是以笛子为主奏乐器的乐曲,多为苏南吹打乐曲牌和少量的昆曲曲牌,其中只有个别曲牌笔者不知来源。例如《洞仙歌》就是。此曲颇受郑觐文重视,1930年3月9日举办的大同乐会春季演奏会上,柳尧章先生就用大箜篌独奏了《洞仙歌》;此曲更是沈知白先生创作民族器乐合奏曲《洞仙舞》的素材。至于普通乐曲,包含了戏曲牌子,如《小开门》、《大开门》;曲艺和小调,如《连厢调》和《道情》;以及丝竹乐《三六》、《四合》等。
上卷既然成卷,就该有足够充实的内容。实际上上卷的内容不仅充实,而且观点鲜明而清新。笔者认定新的观点是什么?原来上卷除讲述了箫笛的源流、演奏要领、一般的演奏技巧和保养知识而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旧式箫笛必须改造的理由,以及他本人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同时还阐述了他认定民族乐器需要“复古”的理由。
从郑觐文讨论箫笛的演奏要领、技巧和转调方法来看,这位“年十二岁已能通普通丝竹”的郑先生,不仅对箫笛制作、演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认识,而且还是相当前卫的。他指出吹笛“更有五要五忌,学笛人尤不可不知道”。这五要是:“一要气长,二要音满,三要圆润,四要沉静,五要悠远。”五忌则是:“一忌急躁,二忌错乱,三忌轻浮,四忌粗暴,五忌油滑。”在讲到按半孔时,他说:按半孔的方法就是“捺住半孔,或将指虚压孔面,使音低下”。短短十余字,其内涵却是很丰富的。
也许有人会说,按半孔的方法不是古已有之?据文献记载,宋“太常笛”不就有按半孔的指法?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朱英教授不也曾提出箫笛上“按半孔”的指法?实际的情形并不那么简单。原来我国历代所用之匀孔笛,是一种莫名的律制。之所以说它是一种“莫名的律制”,乃是因为这种匀孔箫、笛所奏出的音程关系,既不属于三分损益律,也不属于纯律,更不是十二平均律。有人认为它是“等差律”(包括杨荫浏先生),实际上这种关于“等差律”的论述或说明,也都是难成其说的。匀孔箫、笛,既没有明确的生律方法,又没有明确的音准标准,半音、全音没有明确的界定,试问,这种笛的按半孔方法何以能付诸实际应用?郑觐文为了能在六孔笛上吹出准确的十二个半音,将箫笛的制作按十二律校音,并特别强调笛上的第二孔的位置,“改近第三孔三分之一以上”。为了按半孔的方便,音孔“以长(椭)圆形为是”。
关于按半孔的方法,朱英只说:“须按得准确,发声当丝毫无误”③。至于如何方为按得准确?琵琶大师当然说不出子丑寅卯来。而在比朱英提出“按半孔理论”早十年出版的《箫笛新谱》中,郑觐文却说得明白:所谓“按半孔”,就是“捺住半孔,或将指虚压孔面,使音低下”,说得何其明白!当然,要获得如此效果,笛子的制作是关键,为此,郑觐文特别强调,“大同乐会出品方准”。《箫笛新谱》中的一句说明,证明郑觐文早在1924年之前就已制作按十二律校音的笛子出售了。
郑觐文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从乐学和律学的角度对笛(包括箫)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指出,先秦乐器的律和调是十分严格而分明的。这一观点,在曾侯乙编钟发掘出来的今天,是不难理解的;可当年郑觐文得出这一结论,并未见着多少证据。他说,“班笛(即今日所称的曲笛)所有的几宫几调,他的第一个底音有多少高,在从前本来是有一定的。因后来经几次的变迁,再加以制造粗劣,就弄得没有标准了。”这所谓“第一个底音”,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筒音”。
接着郑觐文又说:“到了清朝,就认一支笛说话,一孔领一调,七孔领七调。但是配起十二律来,只有七律了,笛调既不完全,所有一切弦类、管类乐器,也只有七调了。这就是中国音乐退化的大原因(其详另载《中国音乐史》)。今西乐盛行于中国,他的主乐器是钢琴,他的调子是十二(七白键、五黑键),调是调,音是音,与中国古法十二律,毫无二样,比了近代只知七调的法子,完全得多了。”
值得讨论的是,我国古代用三分损益十二律。这是不错的。但笛上最早或先前是否用十二律,或者具备十二律,却是不可相信的。就拿盛行于汉代的笛来说,有的说乃是汉武帝(前156-前87年,前140-前87年在位)时人丘仲所做,有的说系张骞出使西域(前139-前105)时带回。东汉著名学者马融(79-166)在他的《长笛赋》中则明言,乃是西汉律学家京房(前77-前37)根据羌笛改进而成。但是无论如何,这几种笛都不可能在一笛上具备十二律。从《晋书•律历志》的记载来看,汉魏时期的笛,就如同明清时期的匀孔笛(其差别是魏晋长笛为竖笛,明清则为横笛)一样,别说一支笛上不具备十二律,实际上其制作根本就无法与律相合。荀勖同列和讨论笛律时,荀勖就指出:当时所用之六孔笛,“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正因为如此,荀勖才设计了符合十二律吕的“泰始笛”。这种追求“古制”的泰始笛(筒音为角),并未付诸实际应用。为此,初唐的吕才汲取了荀勖制作“泰始笛”经验,又设计制作了符合十二律吕的“今制”(筒音为宫)的“尺八”(由汉魏长笛改进而成)。
就荀勖的泰始笛同吕才的尺八比较而言,尺八远比泰始笛短。现将十二支泰始笛同十二支尺八的管长列表于下,以示比较:单位 尺
律 名 黄钟 大吕 太蔟 夹钟 姑冼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泰始笛 2.84 2.66 2.53 2.4 2.25 2.13 3.99 3.79 3.6 3.37 3.2 3.0
尺 八 1.8 1.68 1.6 1.5 1.42 1.33 2.53 2.4 2.25 2.13 1.95 1.89
《宋书》和《晋书》详细地记载了“泰始笛”的定孔方法,笔者依照记载制作了黄钟至仲吕六支笛,并依“黄钟”律管校音,证明泰始笛是完全可以合律的。可惜《唐书》无吕才尺八的制作尺寸,无法验证。尺八的制作虽然符合了时制,但律制的改动,当时的音乐生活缺少应用新律制的气候,吕才给竖笛所取的名称沿袭了下来,而符合十二律吕的尺八却仍然未被社会所接受。
在《箫笛新谱》中,郑觐文说:明清时期的笛“一孔领一调,七孔领七调”。笔者以为,旧式的匀孔笛,配起十二律来,连七律也无法配准。有鉴于此,郑觐文才十分赞赏使用十二平均律的西洋乐器,尤其是对钢琴更是推崇备至。尽管当年郑觐文尚不知十二平均律乃是我国明代科学家朱载堉(1536—1611)首先发明的(尽管他也研读过朱载堉的著作和“新法密律”),但是他认定十二平均律同三分损益十二律乃是基本一致的。他说:“西乐,非但他的乐器造得精密,就是他的理法,也非常完全,与我们中国的古法,毫无两样;曲谱的法子,也精细。所以我们要振兴中乐,与世界的音乐竞争,非先以复古与改造乐器及曲谱入手不可。”郑觐文认为,“十二平均律”同我国“古法”(三分损益律)是十分相近的。至于“古来十二律的法子,用算学还起原来,总不能齐整”,就像地球自转、公转一样,不必过分吹求匀等。
书中,郑觐文一再强调“旧式箫笛必须改造的理由”。他指出当时的箫笛制作有三大弊端:一、制作前选材太随意,不注重音调同管径、管壁厚薄之间的对应关系;二、各种调门没有固定的音高;三、匀孔箫、笛无法符合十二律。为此,他提出箫笛制作的新主张:一、应以“黄钟”(即钢琴上的C)为标准音;二、匀孔箫、笛各孔的间距应像西晋的“荀勖笛律”所制“泰始笛”,或西洋长笛那样,孔距不必相等;三、音孔一律挖成椭圆形,以方便转调时按半孔。
接着,郑觐文列表再加说明,介绍了一笛“转十二调”的方法。为节省篇幅,现将一笛六孔能奏全十二个调必备的十二个半音的指法罗列于下:
● ● ● ● ● ● ● ● ● ● ○ ○ 图例:● 表示按孔
● ● ● ● ● ● ● ● ○ ○ ● ○ ○ 表示开启之孔
● ● ● ● ● ● ○ ○ ● ○ ● ○ ▲ 表示按半孔
● ● ● ● ● ○ ● ○ ● ○ ○ ○ ☉ 表示按放皆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5 6 b7 7 1 #1 2 b3 3 4 #4
当然,这六孔笛不是匀孔笛。
从以上所列出的指法表可以看出,郑觐文除第一孔用按半孔而外,其余诸孔注重的只是“叉口”指法。叉口音比半孔音的音高稳定,音质也稍优;但指法不及半孔音简捷,音准更需要气口的控制。当然,为了保证音准,无论是叉口或半孔,音高都得凭借听觉的校正;听觉反应灵敏,是吹奏音准的保证。
笔者以为,无论是三分损益律还是十二平均律,付诸于“旋宫转调”的实际运用,都有其不足之处。更何况律学的理论研究同应用实际之间总有差距,如何缩小其间的差距,乃是有待音律学家解决的难题。
在郑觐文看来,三分损益律和十二平均律是相近的;我国上古乐器所用为三分损益律,因此依此律制制作出的乐器便能同西洋乐器相吻合。这就是郑觐文的推理过程,也是郑觐文推崇古乐器的原因。
郑觐文在1924年出版的《箫笛新谱》中,确有重大的失误。这是郑觐文思索未深之证明。前文说过,书中他提出箫笛制作应以“黄钟”(即钢琴上的C)为标准音的主张,而按照乐学理论,笛的筒音应该为“黄钟”,因此他就将笛的筒音定为黄钟,也就是“C”。为了应验这理论,他在《箫笛新谱》下卷的乐曲说明中更作了进一步的剖解;可就这进一步的剖析出了纰漏。例如曲谱《大赐福》,郑觐文所注明的是“无射均”、“bB调”,“旧用正宫调,即四字调”,筒音作“re”;筒音为“do”的《小桂枝香》是“黄钟均”、“C调”。从表面上看,这没错;可结合实际却行不通。何故?请听其详。
原来郑觐文将笛子的筒音定位“黄钟-C”,这“C”乃是音名,并非绝对音高;它该是c2呢还是c1?若是c2,那它就是如今所说的梆笛;若是c1,那就是与如今琴箫同调的F调大笛。细想当年的民族音乐实际,F调梆笛仅流行于北方,根本就不是南方吹打乐和丝竹所用之笛,而筒音为c1的F调大笛,当年根本就没人制作过——当年郑觐文仅制作过筒音为d1的匀孔六孔低音笛而已。
郑觐文之所以将黄钟定为C,可能他认为容易同西洋音乐接轨,就同陈振铎先生曾提出将二胡的内外弦定成c1、g1一样。1924年郑觐文在《申报》上披露这一观点时,柳尧章先生就深表赞同,当日就去拜会郑先生,并结成忘年深交。实际上只要郑觐文先生当时细想想,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将洞箫的底孔定为黄钟C,而将笛子的筒音定为高五度的林钟G不就得了?当然,这问题可能后来还是被郑觐文所认识了。1928年底,郑觐文就宣言又已“考得正确之黄钟,适合西乐A字音义”就是明证。
注释:
①② 见上海音乐出版社《沈知白音乐论文集》中《二十二年的音乐》。
③ 见《国立音专朱英教授发明中国笛上半音》,载《申报》1934年6月11日教育新闻 |